
貫通中西,廣納百川,是香港過去百多年的特色,這裏收納過不少通緝犯、政治犯、落難文人、學者等,也是戰亂時期商人和平民百姓逃難安身之地|他們沒有視西方為「敵對勢力」,反而創造了不少中西合璧的輝煌成果。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馬照跑、舞照跳」便算數?當然不是,港人最關心的,恐怕是對私人財產物業的三權保證、和法治下享有的既有自由。

在共產主義創始人馬克思200周年誕辰前一天,中共在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大會,中國也向德國贈送馬克思雕像。中共如此高調紀念馬克思,當然不是沒有原因和目的。

特朗普應該知道是美國在討這個世界的便宜,不是世界在討美國便宜,他此番把關稅倒行逆施,遭殃的是自由主義!

民粹主義者反權力精英,對外則仇外及排外,傾向孤立主義的狀態。學術界至今似乎還未找到一個簡單而精確的定義,來界定民粹主義,也頗難界定本土主義。

全球化顯然是一個遠為複雜的過程,誰是受害者以及受害者?並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問題。

貧窮問題,自古代帝制出現後,因尊卑貴賤之別而出現弱勢社群,造成貧窮,中外皆然。只要弱勢社群的謀生權利、謀生機會和謀生空間得到保障,就可解決,但資本主義做到。

香港營生環境及謀生空間不足,是資本主義市場極化所導致,這才是社會不和的深層次矛盾。

今天消費主要在歐美,財富也集中於歐美,形成了全球貧富不均,和全球消費不足。

特朗普胡作非為,看來會受到選民的懲罰,但事實上他的狂妄作風,早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表露無遺,美國人民卻依然用選票把他送進白宮。

今天政府可掌握所有市民活動的大數據,稅種和稅率都可以不用粗糙的一刀切,而作更合理和細緻的劃分和抽取,並作跨地域的全球抽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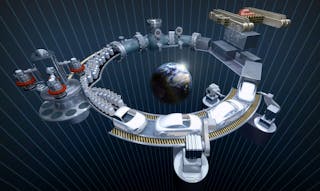
過去二十年來,大型跨國企業的急速擴張,主要是靠着扭曲法律、政策與市場監管來達成,而政府還爭相加碼,乖乖捧上「朝貢禮單」。

世界上其他的灣區城市群,起初都是自組織的;政府只是在中後期,才在政策上加以配合罷了。

如果可以像開放改革初期實事求昰看中國自己、香港與世界千百年的人文全景,說不定可以在最高層次校正座標方位、輕輕撥亂反正,借助中港大同大異的互用互補取得共識共贏,世界也可能蒙其利。

在面對政治環境改變、周邊地區關係轉變,以這種「不變」的思維來面對改變,顯然是不足夠的。

中國要對人類做出大貢獻,必須做好目前自家的事情。

若把一國兩制看作是敵我對立,那是冷戰思維,盲目的意識形態。

今天新加坡成為相當一部分香港市民羨慕向往,乃至移民目的地。

當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後,村裏那些農村幹部,能工巧匠及善於經營,敢闖敢干者,各自發展。

香港的中下層宜盡快學會一些機械人沒法掌握的技能,否則命運可悲。

回歸20年來的發展,跟這美好願景有頗大落差。

在多數年輕一代的香港人之中,大多沒有太認真想過一國兩制的「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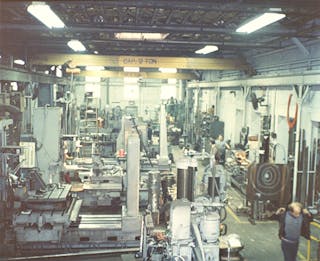
如何把田耕得更好,答案自然是搵牛,可如果我們問如何提高服務競爭力,答案是是讓馬發揮它的能力。

六七暴動的狂熱簡單幼稚愚昧,不單是方法錯誤,歷史進步的方向也錯誤,實為「超級極左」。

我特別用「找尋」這個詞,因為覺得傳統逐漸消失。現代生活的意義就是「斷裂」,外國如此,中國也是如此。

金融化就是把所有東西化為數字,身為人我們會考慮人的關係。金融化令我們愈來愈不似人形。

這個大概說明,在這個時候,當然也難怪世界已經拉不動中國,因為中國規模太大了,只有她反過來拉動世界。靠外貿的增長來拉中國經濟,已變得愈來愈難,因為她體系太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