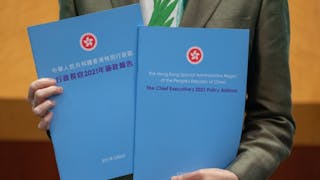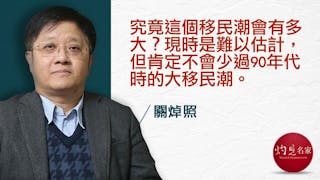馬時亨表示,香港需要改革,建議積極推動貿易數碼化,並改革公共財政系統,最終實現量入為出的平衡預算目標。

政府擬大舉發債推進基建,唯經濟前景不明朗,令人憂慮公共財政狀況。財政司長指債務比率可控,但未計及非顯性債務,如退休金等。社會資源運用效率亦受質疑,諸如西九文化區需出售住宅維持營運等問題。政府應制定更透明的財政指標及有效運用資產,而非單靠發債解決財政問題。

香港現在正處於回歸以來從未經歷過的大變局,政府必須再來一次長遠公共財政大檢討,從收入和開支兩方面重新評估香港的處境、面對什麼風險,以及應該採取什麼對策。

香港公共財政陷困境,儲備急降。財赤是周期性還是結構性?本文分析指出,地緣政治變化、內地經濟波動及人口結構改變,令香港經濟模式不再,財赤恐難短期解決。重塑國際角色、改善財政紀律、提升生產力,方能應對挑戰。

本書稿件《Modern Corporate Finance》以西方視角詮釋中國大陸公司金融,恐有失真之虞。專章引用投行家Carl Walter觀點,聚焦國企治理缺陷及金融體系脆弱性,值得商榷。讀者宜保持批判性思考。

公共財政緊絀,本文續談開源節流。開源方面,建議違建可有條件合法化,並補徵差餉地租;政府應善用閒置官地。節流方面,不應停聘公務員;亦不應加利得稅,宜取消標準稅率,提高最高邊際稅率至20%。所有措施須考慮社會成本效益。

改善公共財政的關鍵在於開源節流。我們的策略是以節流為主,首要是在維持以至改善公共服務的前提下,管控經常開支增幅。

如何在保持財政穩健的同時,靈活應對經濟和社會需求,是政府需要面對的重要課題。基於《基本法》第107條的原則,香港公共財政須提高財政收入來源的多樣性等。

特區政府和管理局未必能將其他地方的設施財政管理照搬到文化區,但參詳海外這類計劃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說不定可以找到靈感,以合適的方案把西九文化區從財困拯救出來,讓它在天下間拼出個名堂。

2024年是香港復常的第二年,大幅度更改稅制似乎不是時機。但一些多年未調整的政府收費,應按照成本升幅,以及考慮市民承擔能力,向上調整無可厚非。

按《基本法》量入為出的原則,特區的財政預算須「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但事實卻是,香港已在4年內有3年錄得赤字,現在看來,回復預算平衡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要真的做到「由亂轉治,由治及興」,關鍵在於包容及凝聚社會,公關和派錢都解決不了管治深層次矛盾。

有人批評政府,實際上仍在推行高地價政策,否則為什麼不按市場意願接受的價錢把赤柱豪宅地出售,任由其流標?

如果政府未能對5年經濟增長率作出合理的評估,又如何能保證經濟政策及財政預算案能符合《基本法》?筆者認為香港也應設立預算責任辦公室,作為維持財政紀律的重要內部制衡制度。

綜觀特首李家超早前公布的《施政報告》,他就公營房屋政策方面,示範了公共行政績效管理的執行。但與此同時必須指出,報告亦突顯了績效管理的落實,鮮見於其他政策範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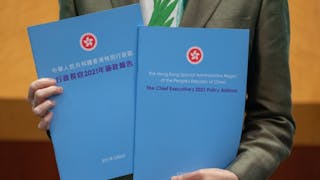
政府不時外聘顧問公司進行長遠發展規劃硏究,但絕大部分涉及基礎建設和土地規劃,較少關係到社會及經濟政策。香港高等學府擁有一流的學者,他們的角色去了哪兒?為什麼又不採用民間智庫的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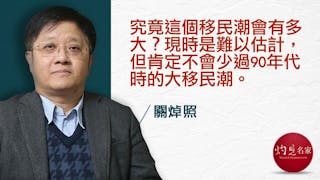
今年的人口收縮現象絕不是一個太大的意外,始終由今年2月至今在香港爆發的疫情對人口增長產生顯著的壓抑作用,但最重要的訊息是,即使疫情過後,香港的人口增長會否短時間內回復正常?

香港公共財政會否因融入國家發展規劃而持續好景、年年盈餘?還是會如《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報告》的預測,在10年後就會用盡財政儲備?

公共財政貴在重實效、看成績。從港英年代開始,香港的預算案已有一個固定模式,要新也新不到哪裏。除非完全推倒重來,否則誰做財爺,來來去去都會是那幾道板斧。

作為前長策會成員必須向公眾交代一個事實,在制訂十年房屋供應目標時,長策會已考慮過相當多的因素來作出預測。

政府現已擁有巨大的財政儲備,可應付將來不時之需,現時政府的財政政策是否可以更進取一點?

不管你是否凱恩斯信徒,請不要忘記減稅亦有減稅的乘數、派錢亦有派錢的乘數。

曾俊華沒有守財或慳錢,只是用錢可能不夠多,更是把不少錢用錯地方。

任志剛提議公共財政收支平衡應該以經濟周期計算,但這做法是不可能採用的。

政府應該未雨綢繆,採取適當措施,避免香港日後要舉債渡日。

社會福利及衛生服務開支佔政府經常性開支超過20%,所以人口老化會對這方面的開支構成巨大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