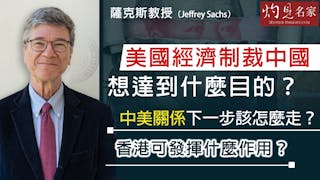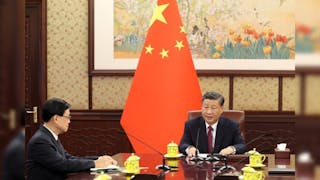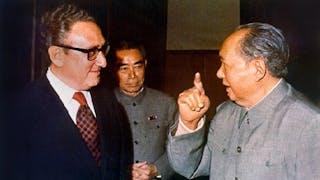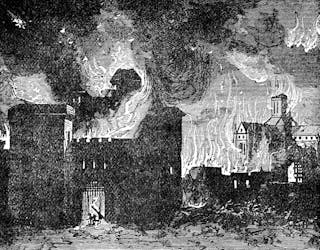新自由主義的失敗、新冠大流行和戰爭使全球進入了一個動盪的時代,與大穩定時代截然不同,這個時代沒有什麼是理所當然的──新的地緣經濟和新的地緣政治。香港與其他地方也一樣,在渡過洶湧的波濤時,將面臨新挑戰。

現實中尚有殘餘反中亂港分子,應付這個複雜形勢一定要斬草除根,不許死灰復燃。為達到目的有多種方法,可兼容教化及徹底消滅兩個極端,及其中的變奏。採取一刀切趕盡殺絕需要付出不少社會代價,實在划算不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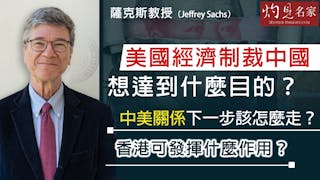
加徵關稅、對華晶片封鎖……中美貿易戰戰況不可謂不慘烈。華盛頓到底想從北京得到什麼?薩克斯教授對中方有什麼建議?中美關係接下來會走向何處?一起聽聽薩克斯教授的分析。

從發展商及某些團體的角度看,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卻是香港健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樓巿下滑時種種問題便更凸顯。說香港成也地價、敗也地價,讀者們同意嗎?

不是說中國完全沒有債務問題,而是西方媒體所言,似是病入膏肓之人反而對患上普通感冒之人指手劃腳,說他們快要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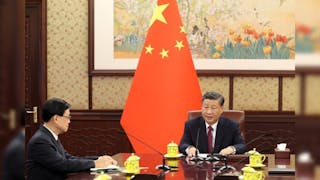
港澳兩位行政長官向習近平主席述職,有趣的是,內地方面高官雲集,包括國務院總理、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召集人、中央統戰部長、中央政法委書記等。這顯示中央政府對香港、澳門事務的高度重視。

現實是我們儘管向外宣傳香港還是奉行普通法的國際金融中心,但西方傳媒並不接受,繼續以他們的價值觀為依歸。說好香港故事任重道遠,荊棘滿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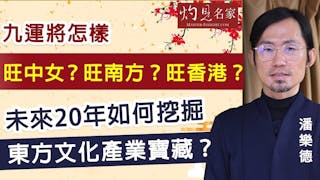
2024年將進入三元九運中的下元九運,九運在術數上有什麼特別之處?術數名家潘樂德指出,九運女性地位會提升,而世界運勢將由西轉東,一起聽聽潘老師精闢分析。

在不少長居海外的好友眼中,香港這顆東方之珠依然光亮。購物天堂、美食之都,有賴良好治安支持,香港始終是亞洲最安全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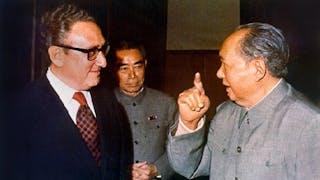
關於基辛格與中國,史家津津樂道的都是他「詐病」飛往北京密會中共領導人,為中美關係破冰打開第一扇門。環顧現今西方國家,還有哪一位政治人物能夠稱得上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會不會是最後一個?

資本市場是主要服務三個個體,分別是企業、個人和政府,這三者是同時既是資本的使用者, 亦是資本的提供者, 當中又以企業的角色最為重要。

寧德時代落戶香港,毫無疑問有着亮眼的前景,但在中美博弈的政治現實下,與美企有合作關係或先進的中國企業都可能被美國視為「眼中釘」,華為已是前車可鑑,對寧德時代可能被推到風口浪尖,也應有心理準備。

若以個人計,香港人的平均投資能力比很多歐美國家都不遑多讓。可是,香港只有750萬人口,整體力量實在有限,無力單靠自身的力量去打造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在這種情況下,必須爭取到歐美資金重返香港。

對於抹黑造謠,政府公開反駁,堅決反對,固然重要,但對方攻擊不斷,恐怕在邊際效應下,作用只會愈來愈小。要如何為香港重拾形象?然而,由當事人向外宣傳,總予人賣花讚花香的感覺。

馬拉松作為參與人數眾多的體育活動,日後「大灣區大滿貫」可由香港牽頭主辦,因香港的海外跑手佔比較多,所以是最有條件造就這項既國際化,又屬區域性的體育盛事。

美國在戰後環球金融貨幣體制的位置,並不是完全出自它的要求,在某程度上,是由盟國加諸在它身上。長遠而言,美國是否最適合擔當有關角色的國家,亦是有商榷空間。

正如沙特阿拉伯公共投資基金(PIF)的負責人指出,這次在香港推出產品,為亞洲投資者打開了解當地發展故事的一扇大門,也讓他們更深入了解到本港連通國家和世界投資者和金融市場的「雙門戶」角色。

減價沒有人會嫌多,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會問:現在經濟不景氣,為何兩電仍要提高基本電費?答案可以用「能源三難悖論」(The Energy Trilemma)來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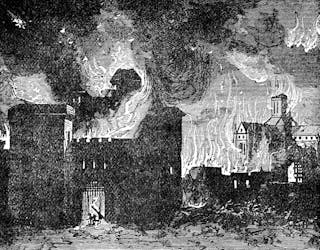
自八十年代中其金融業出現以「放鬆管制」(de-regulation) 為主調的「大爆炸」以後,倫敦是能把握「石油美元」流入歐洲的契機,逐步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美元中心。

世界技能大賽一直緊貼科技發展、回應行業及社會的人才需求,讓年輕人在其工作和技術領域提升技能水平,了解行業趨勢,拓闊未來發展空間。

譚盾一直在思考東西方音樂不僅需要碰撞,還需要大膽地嫁接和勇敢地重生。他覺得或許搖滾就是一個從觀念到音樂的全方位的突破口,於是譚盾將古典音樂的圖騰──巴赫,與大自然的圖騰──成吉思汗融入到創作中。

大眾傳播學學者麥克盧漢(McLuhan)說,媒介是身體的延伸,他還說,媒介即信息。對於媒體人來說,手機已經成為身體的一部分,永遠保持手機在線,既是工作需要,亦是生活狀態。

APEC大會安排了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坐在習近平左面,此舉似乎另有玄機,一方面它肯定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國家的關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香港的國際地位是被全世界(包括主辦國美國)重視的。

如何在保育和安全、發展之間取得平衡,從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政府固然首要考慮保障公眾和遊客安全,但採取一刀切清拆的做法,肯定不會符合社會期望,亦不符合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

一年過去,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接受廠商會會長史立德訪問,分享特區政府的最新工作,以及如何將習主席的期望落到實處。

或許有人覺得,貸款人應自己承擔貸款的風險,怎可以要求政府出手救市來幫助他們擺脫負資產?這對未買樓的人不公平。然而,負資產除了會增加社會的金融風險外,還會破壞社會的內需,令經濟停頓不前。

假如這次何君堯一舉得手,便很可能演變成一場極左保守勢力用來肅清異己的「整風運動」,且會令外界誤以為香港社會價值急速左傾,到時候香港在中美關係中加強民間交流或發揮橋樑作用,便無從說起。

可是,這一切現在都近乎徹底消失──議員、政黨、仍然生存的社會團體,大多是讚好、擁護,異議或批評聲音弱不可聞。這種「和諧氣氛」,到底是真正和諧,還是群眾有話不想說、不敢說?

只要香港人不要自大、不要懶惰,憑着「明天會更好」的信念,增強對香港的歸屬感,今天,只是下一場精彩比賽的起跑線。

區域經濟對香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跨國公司在香港無法像在上海或北京一般建立對內地以及全球市場的理解。假如這些方面不能解決,跨國公司將缺乏來港建立區域總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