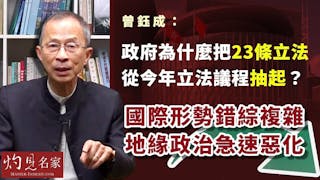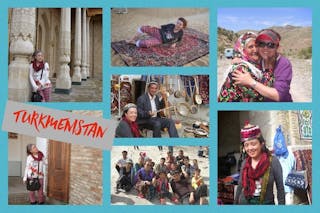行政長官李家超對獲聯合國不同機構委聘的12名香港年輕公務員,提出若干「寄望」,特別是要求他們「肩負起說好香港故事的責任」。可是這良好意願看來值得商榷。

大陸一直反對外力介入台灣,但美國及其盟友對台售武、加緊圍堵中國也一直沒有停止過!這種對着幹的形勢,最終可能會重蹈俄烏戰爭覆轍,台海終於難逃一戰!

疫情放緩政策改動,赴日旅遊重回生活後常聽到人們不諱言,把「去日本旅行」稱作「返鄉下」。本來當作一句戲言並不成問題,但真正問題是,他們講的時候是很認真的!

愈來愈多的公司也意識到,中國已經成為了創新的靈感和知識源泉,並且如果想要在中國獲得成功,他們需要深度理解並參與進來。對於其中一些公司來說,中國戰略甚至是他們全球戰略的核心,當中包括什麼?

今年的《施政報告》中,特首李家超特意強調了吸引人才對香港目前狀況的重要性。新加坡被認爲是香港引進人才路上的主要競爭對手。這樣一個彈丸小國,為何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呢?

法庭總會說年輕不是藉口,又會說犯了刑事罪行便要負上刑責,但也要看看在幕後秘密地策劃、慫恿、煽動、安排、提供物資的人的責任。

經過3年的疫情打擊,加上全球政經環境大變,疫情過後,更大的震盪也許才剛開始。而全球產業鏈重組、美歐全力「去中國化」,都動搖了我們過去對政經世局的認知。在這個大時代,政府的領導能力特別重要。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所長陳志武教授出席灼見名家八周年論壇時表示,2022有三件大事改變了世界局勢,令中國經濟過去40年增長所依賴的條件改變,「只談生意、只談賺錢」的國際規則已成為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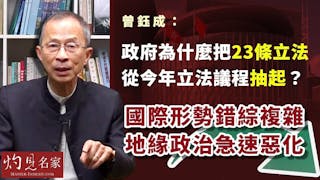
政府把《基本法》23條立法工作從今年立法議程抽起。前立法會主席、香港政策研究所副主席曾鈺成認為,過時草案無法應付新的國安問題,因此需要撤回法案修改。為何不能先立法後修改?一起聽聽他的分析。

中國的宏觀環境在不斷的變化和發展中,因此企業戰略家必須採取非線性、多維和跳躍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

不少跨國公司已經認識到了有效利用中國市場機遇及應對競爭挑戰的方法。當跨國公司在中國的認知不斷演變之餘,他們考慮的因素亦在不斷調整,思考探索着更基本的要素。

估計中國人是不敢放大量資金在新加坡,就算香港人可以去新加坡工作,新加坡政府都是得物無所用,那些去了新加坡工作人很快就會被踢走,咁危險的事,唔會有太多香港人願意去新加坡工作。

「後疫」並不等於回到疫前;「疫後」往往意味着疫情完結後,打掃災場。「後疫」卻代表着迎接一個新的時代,和以前完全不同。

筆者希望新任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能借力香港國際創科中心,引入更多內地及國際創科企業來港落戶發展,推動香港再工業化。

中國近代史與現代史刻劃着中華民族變法圖強、洗刷百年國恥的嘗試與苦難,本質上是為了令國家擺脫明清時代的厄運,以達至民族復興。可是,現在國家卻有可能在重蹈明清時代的覆轍,這無疑是對歷史的一個極大諷刺。

中國的創新降低了先進技術的成本,並改變了許多人的生活,而這些改變亦可讓RCEP成員國受益匪淺。中國企業在繼續投資這些市場的同時,亦可促進區域的本土創新,支持這些經濟體,改善它們的公共服務。

事情總有正反兩面,人類的工業化也是。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財富和生活素質得以提升,但武器的發展也愈來愈精良,武器的款式也層出不窮,潛在損害大。作為世界領袖,應帶領人類作出一個最佳的未來發展選擇。

隨着時間的發展,這些情景將會怎樣演變?許多跨國企業和中國企業的管理層人員和智庫及研究機構亦曾與我交流過。可以說,大家的觀點各不相同,眾說紛紜,都自覺是有理有據的。

下一屆的香港特區政府要建立的並不是一個「舊的CPU」,而是一個具有整體和超越過去眼界和視野的能力,加上能協調強大執行力的新戰略規劃能力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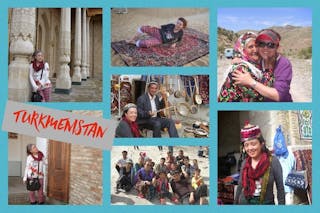
我一直渴望去敘利亞和伊拉克,那裏的古代歷史建築和文化,我一直嚮往,那一次在德克蘭機場,看着航班顯示牌出現這兩個國家首都,心裏面忽然興奮,在我的腿還可以走得動的日子裏,還可以去嗎?

美國極力拉攏印度,印度卻進口俄羅斯原油。對它來說,若不想當棋子,就要在兩強間抗衡,博得最佳利益。

時鐘不能回撥,不能夠再問當時如果西方政客在歷史的深度中更深思熟慮一些,可不可以避免今日的慘局?

冬奧強調了中國是國際的和平建設,進步力量,與世界各國一起向前。中國的冬奧,美國的烏克蘭行動,一起重新把世界劃分。

亞太經合組織(APEC)企業領袖高峰會周四(11日)登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講話,他表示,早日走出疫情、經濟穩定復甦是亞太地區目前最急迫的任務;亞太地區不能也不該回到冷戰時期對立的狀態。

鄭永年建議,中國在南海不應過度關注軍事、地緣政治等問題,而應更關切經濟問題,通過在南海、湄公河建設開放型經濟圈。中國也應與東盟建立開放包容、不針對第三方的新型多邊關係,聚焦解決區域問題。

有道是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美國迫不急待向剛剛把美軍趕出阿富汗的塔利班示好,而且由五角大樓兩大巨頭出面,原因可能有3個。

哈佛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認為,在這場地緣政治大賽中,美中兩國能否找到一種方式,構建並管控一場有建設性的競爭,並讓兩國竭盡全力去展示哪一種制度能為人類帶來更多福祉?

組織架構、創新能力、人才建設等企業的基本面依舊是立足之本。在此之上,企業需要有足夠的憂患意識和進取心態,在動態的發展過程中同時具備宏觀的戰略思維以及微觀的落地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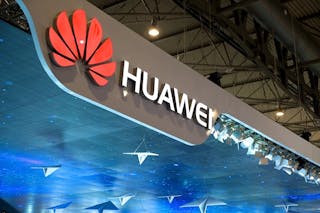
在約束條件下,憑對新發展大局深邃的預判,尋找新的機會,找到後儘快跳躍和重點執行,建立能力(包括通過全球資源平台的組建和生態系統),進行成功跳躍,即是戰略的第三條路。

中國絕不能四處樹敵,我們也需要思考為何中國在40年難得的發展機遇之後,我們會陷入這樣的包圍圈,甚至在我們的周圍已經形成了美日澳印四國的準同盟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