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實幸福,就隱藏日常生活的點滴中。當我們睜大眼睛,留意周圍的人事物,自然會發現,美好,無處不在。

媽媽生活的這個大時代,中國由農業社會進化成工業社會,並以快速的步伐邁進信息社會;香港則由英國管治過渡到國家管轄的一員。而一個讀書不多,卻對家庭和子女有高度承擔的女性,能夠成功跳出農村到香港這個大都會,後來還跨越到地球的另一端,不愧是一名時代女性。

隨着父母離世,身邊的長輩已經一個接一個離開。不知不覺間,我跟外子也成了長輩。開始有人到咱們家裏拜年,要張羅食物煮什麼年糕,都成了我的責任。而每逢佳節,腦海就會浮起昔日跟爸媽過年的熱鬧場景,如今卻成了往事如煙。

在想讓每個人都開心的情況下,我犧牲了最要緊的事。反省之後,我發現了這個重要的教訓:如果你不替自己的生活排定優先次序,別人就會代勞。

在資訊爆炸時代,孩子獲取資訊管道多元,視野更廣闊。相對上世紀50至60年代物質匱乏的兒童,現今孩子面對的挑戰更偏向心理層面,家庭和學校應共同努力,引導孩子建立自信,培養面對挑戰的韌性。

周休三日的好處多不勝數:多休息、多了時間跟家人一起(甚至有建議說可以鼓勵生育)、更多時間參與義工、吃喝玩樂的時間也多了。

王耀宗先生回憶1961至1971年在灣仔的童年生活,描述住家環境、學校點滴、家庭成員與個人成長經歷。從筲箕灣搬到灣仔,就讀高主教,適應英文學習的挑戰。

命運,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我了解的只有:人生是長跑,大家都在跨欄。有人跌到了,有欄撞倒了。有時有觀眾,有時一場空。姿勢醜一點沒關係,氣勢還在就好。

去年女兒代表學校參加第一屆「腹有詩書」比賽,時隔一年,我再次坐在台下觀賽。當日會場内嘉賓雲集,學生竭盡所能,比賽氣氛相當熱烈,讓我們經歷了一次很有意義的文化之旅,也令我對本地古文教育有一些觀察與感想。

「家」是什麼?「家」在哪裏?家人能團聚多久?「家」的土會灑向何方?清明假期,祝福每位朋友,安然回家。

今年疫情可能還過不了,但是只要有朋友,就能歡笑。對抗疫情這個方子是最有效的,就讓我們從朋友和歡笑來好好地過這一年吧!

夫妻既是同林鳥,遇到疫情就更應該把彼此當成「盟友」,一同商討面對疫情的回應,如彼此在家中的分工,對整潔的要求等。疫情下,家是另一所學校,讓家人患難見真章,然後重新學習如何相處的試場啊!

放在元宇宙的世界裏,系統沉浸就是你和該平台的合作和平台給你的回饋有多緊密。這種沉浸感亦不一定要在元宇宙的世界才能領略, 我們身處現實世界,經常會感覺到自己和周圍環境的關係。

其實,夫妻在家中是一個團隊,大家彼此合作補位,一家人才能相處融洽啊!

我絕對覺得往昔「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已不合時宜,需要重新檢討。而在這個雙職家庭愈來愈普遍的年代,家務事更需要夫妻一起分擔。特別在教養孩子的路上,爸媽若共同培育,孩子才能在父母的蔭庇與督導下茁壯成長。

日本作家曾野綾子描述這類人的時候,有這樣一句︰「自私自利是一種病嗎……當自己有苦要訴時,認為大家都必須馬上放下手邊工作,專心傾聽才是。她們看來,常常像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一樣。」

90年代,兩位驚動文壇的妙齡少女在上海火車站初次相遇,討論着對未來的憧憬、寫作的熱情、內心的壓抑等。她們是迥然不同的人,卻又惺惺相惜。

家不是法庭,別只看對錯,家是講愛的地方,是培養歸屬感、平安感的原點。

丈夫失業了,這是不少太太的噩夢。做為太太可以怎樣面對?

英國話自己好心才推出BNO計劃,或者的確是好心,但可能好心做壞事,拆散了不少家庭。

筆者認為,學校還會存在,而且擔任關鍵的角色,但是勢必會脫離包攬學生學習的角色,因為不是任何意志或者政策可以左右其發展的。於是必然會出現教育的新生態。

上世紀八十年代有名的香港電台夫妻檔張文新、車淑梅分享婚姻法則和教子良方,以「半熟」定義夫妻關係,稱對子女要「掌聲勝過怨罵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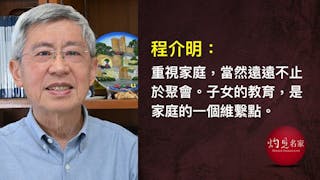
所謂「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可以有不同的闡釋。甚至同樣的現象,可以在字面上有相反的闡釋。

情緒智慧是把智慧加添在與生俱來的情緒。提升情緒智慧是提升人生成功的因素,邁向快樂的人生泉源。學校及家庭是情緒教育的起步點,第一個教室,父母和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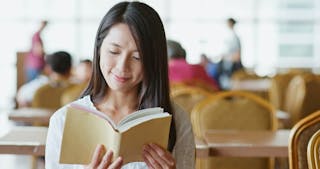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女人與什麼人相處,便會把自己塑造成什麼人。想看一個女人的涵養,只要看看她的社交圈就足夠了。

不抽菸,是保護身體不受傷害;不飲酒,是希望常保心智清醒,不至說錯話、做錯事。

俗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行孝並不難,好好地調伏心念,守規矩、合道理,照顧好自己,也幫忙父母分擔家務,從這些小地方就可以做起。

正如大自然有高山、溪流、大海,展現高低錯落之美;家庭裏也要有對長輩的尊重,才能展現人性之美。

行佛所行:福慧雙修,悲智雙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