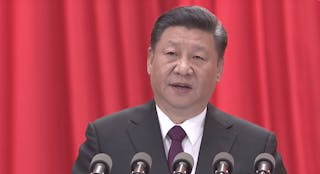我相信,珠海和香港這兩大城市,必將在大橋的帶動下,互相融和、經濟合作、飛躍發展。

作為大學校長,我深知創辦高等教育機構的困難和責任。理大決定與深圳大學合作創辦大灣區國際創新學院,就是在大灣區發展的大前提,深化港深創新合作的模式。

浸會大學榮休校長陳新滋教授認為,如果每個人只考慮自己的利益,不理睬別人。香港只顧香港事,結果香港連自己也發展不好。將來要做好粵港澳大灣區的話,九個珠三角城市和兩個特區一定要互相幫助。

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的角色,需要執行國家交付的任務,任何香港特區政府需要付諸實行的政策、任何機構設置以至財政撥款,最終還需要立法會通過,最後還需要在香港原有機制中運行。

期望應屆的畢業同學,銘記「植根香港、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奮鬥方向,顧己及人的人生態度,毋負特別有意義的2018年。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表示,中美貿易摩擦對香港帶來的負面影響並不大,但中美貿易戰一旦爆發,香港遭受影響將不可避免。

中國只有全面深化改革,在國有企業的改革、財稅改革、金融改革、土地改革等領域,涉險灘啃骨頭,實現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才有出路;香港有實力謀求自身的新發展,為國家開放作出卓越貢獻。

中國為了推動經濟全球化,現正全力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區。面對新政經格局,中國將會遇到怎樣的市場機遇?中國的政策、制度體系將會有怎樣的創新改變?

中央政府官員的特點,是官僚的思維,凡經中央制定的政策,就必須具有權威,即不容隨意提出修改意見,但大灣區牽涉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際聲譽,實在不容有失。

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從媒體所見,似乎重心在深圳,一是深圳與香港合作,另一是深圳向東擴展。

客觀的經濟環境,正在落實「命運共同體」的成長。若要東方經濟圈進佔王者寶座,應發揮灣區作為支撑地的棋子作用,加快走出數字絲路的創新棋步。也許,是大家另一次提出想法、另一次建議規劃的時候了。

香港作為區內市場開放、法治、經濟環境最完善的城市,在國際接軌、監管制度、市場體系等「軟實力」方面,仍是大灣區的重要國際平台。內地企業可以依託香港,加強參與全球化經濟,走向國際。

陳爽表示,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中,台灣並非旁觀者,而是合作夥伴。共同參與大灣區,建設符合歷史進程,符合合作原則,具有協同互補的優勢。

城大出版社舉辦新書發布會暨公開講座,邀請了中原集團創辦人施永青先生就「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角色」,與城大公共政策學系李芝蘭教授來一場精彩對談。

梁錦松認為現時全球的競爭格局已由國家之間的競爭,轉為城市群之間的競爭,未來香港於粵港澳大灣區的定位不應局限全球金融中心,亦應作為人才中心,為中國吸引來自全球的人才。

究竟第三回合的區域融合將會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大灣區是一個什麼概念。

下一步我們不妨問問,既然有了經濟,地理和理論作支撐,我們會不會得到政策方面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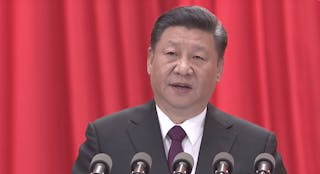
國家主席習近平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總理李克強把粵港澳大灣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要堅持一國兩制。港人來內地工作和居住,會獲國民待遇。

李健麟認為亞洲東南部的大灣區的敲定,對香港中長線來說無疑是好消息。大灣區的概念是世界一體化的潮流,是強強聯合。

中國是全球經濟活力最強的地區,「背靠內地、面向全球」無論過去、現在、未來都是香港經濟金融發展的磐石。

隨着世界經濟及貿易延續2017年可觀增長,與及粵港澳大灣區和香港-東貿自資協議落實,雖然金融局勢較難預測,2018年香港經濟仍可審慎樂觀。

匯豐銀行亞太區顧問梁兆基認為,大灣區的發展最重要是建設完善的交通網絡及生態圈,從而驅動區內各城市善用本身的產業優勢。互相融合,產生更大協同效應。

HPV是引致子宮頸癌的一個重要因素。凱普生物把香港大學的醫學科研成果產業化,十多年來碩果纍纍,香港企業是否可以從中得到啟示?

容蔡美碧強調,基金會希望從經濟、社會民生、科技、跨代共融和身心福祉五大方面構建一個框架,供政府參考制訂政策、同時供企業和科研機構針對高齡化進行產品和服務創新。

「大灣區的建設是百年大計,不是五年內便可完成的壯舉,而是需要每一代人不斷地耕耘。」

2018年香港的政局漸趨穩定,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漸漸提高。香港應該利用國家的優勢和機遇,重拾國際化的發展,特別在思想行為上,認識文化態度的轉變。

國內的電商發展都特別快,隨著互聯網和物聯網的發展,基於電子技術、信息技術的世界貿易格局會有非常大的變化。

回歸另一個十年,隨著國際環境的轉變,香港和東南亞新興市場的經濟繼續反覆,另一個金融風暴日漸靠近。

林家禮認為,1000間公司只是起點,突破2000間固然是將來的目標,但強調未來除了談量,也要談質。

世界上其他的灣區城市群,起初都是自組織的;政府只是在中後期,才在政策上加以配合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