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峰會將會進入史冊。而峰會的順利舉行,突顯了香港的優勢﹕開放、高效、認真、勤勞、做事一絲不苟。在學術方面,同行評議的制度是公認的標準。徐立之說:「香港可以做得更多。」

My friend, colleague, teacher and guide, Ming K. Chan, is sorely missed .

「我們着眼於成立大灣區國家實驗室的可行性,把不同學院放在一起,發展跨學科研究,更引進企業家精神及經驗,與工業界合作,展望未來港大在這些實驗室會扮演重要角色。」

陳明銶一生無兒無女,感念他像一枝蠟燭,燃燒自己的生命,照亮後學,不遣餘力!堪稱香港之子!

史丹福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傑出專家陳明銶教授追思會昨天假香港大學王賡武講堂舉行,逾200人出席。陳明銶教授生前同事、學生、好友及政商各界人士共20人分享與陳教授交往的點滴,場面溫馨感人。

香港大學即將開辦的6個文理學士課程,透過着重跨學科學習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希望培養具國際視野和跨領域思考能力的明日領袖,以應對未來社會的挑戰。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樂見《百年巨匠》紀錄片拍攝饒宗頤教授的生平、事蹟,讓更多人能認識到才情橫溢、學藝雙攜的饒公,同時借助紀錄片傳誦他深厚的學養內涵、嚴謹的治學態度和弘揚中華文化的堅定決心。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副院長梁雪兒以四大範疇講述港大醫學院過去成就,包括傳染病監測及控制、肝病的新治療方法、治療脊柱側彎,以及基因診斷和癌症精準醫學方面發展。

徐立之教授是生物科技的權威專家,他作為呂志和獎董事會的成員,有沒有對獎項有任何建議呢?

目前港大的管理團隊都是前兩任校長招聘及委任,張校長走馬上任,是否需要建立自己的班子,推行他的鴻圖大計?

論者一般甚少談到傅秉常與香港的種種關係,而這一部分卻是傅秉常研究的重要一環。本書嘗試根據各種原始資料,填補這一缺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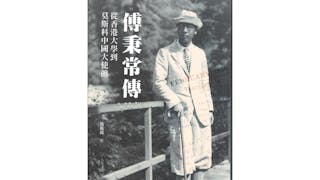
筆者希望透過這部傳記,探討傅秉常這位具香港背景的粵籍社會精英,如何參與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由此反映香港在中國近代化中所擔當的角色。

香港其實已經潛伏了高等教育供不應求的跡象:一方面,是社會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另一方面,是高中畢業生升學的需求,上下夾攻。

要令部分年輕人不要去思港獨,唯一的方法是讓他們至少恢復對特區政府維護港人身份及香港核心價值的信心。

我相信張翔也知道香港兩極化的政治環境會繼續影響、甚至衝擊大學。我也相信,他正在深思應對之道。目前,他像是對支持者和懷疑者說,讓我們提高視野、發揮抱負,專注於尋求真正的國際卓越,為香港和世界作出貢獻。

7月17日是張翔教授履新港大校長的一天,他在百忙中抽空來到利瑪竇宿舍,發現自己和香港大學的緣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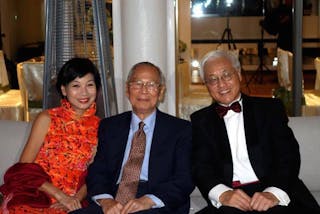
譚廣亨教授強調醫科是一個科學和人文學並重的學科,當一名好的醫生不僅要醫術精湛,而且要醫德高超,要有仁心,也要有很好的溝通能力。

「教育可以改變人生,也可以改變社會!」譚廣亨教授認為教育應該放在個人或社會發展的首要位置。

香港政府從來就沒有對高教大學有所干預,一點也沒有,這是幾十年的傳統。我在港大的時候,從沒有試過政府要求我們做什麼,完全是由我們自由的發揮,完全是靠學者自己的經歷、精神、學術興趣。

高亞培博士著寫了一本勵志手冊,跟時下年輕一代分享自己的人生經驗,讓迷茫青年面對社會不公、經濟不景氣、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的考驗時迎難而上。

中學改制,由七年變為六年,入讀大學,須多留一年,這增潤學年,讓同學有機會去充實自己,認識醫科以外的世界面貌。這人生體驗,對一個人的成長,極其重要。

香港也有隱憂,高校研究水平雖然不錯,但吳校長認為如果繼續這樣發展下去,未必能夠維持現狀。

港大經過這幾年的折騰,元氣大傷,希望新校長能夠帶來新氣象,大學可以減少爭鬥,向前推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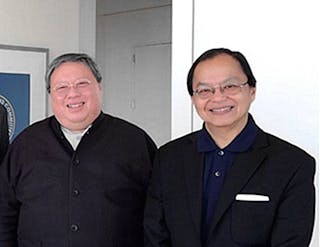
筆者有幸認識祥安兄,彼此有緣,偶有相約茶敍,話題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收穫甚豐。如今祥安兄離去人間,筆者痛失一位好友。

香港大學任校長譚廣亨;「香港大學一直透過不同的渠道,以知識推動社會發展,當中有也有頼與傳媒建立互信的關係,才能與市民分享知識和研究成果。」

雖知往生是不知什麼時候發生的必然現象,也預計無常是隨時隨地發生。然而,今早得知博學而可親的饒公往生淨土,心中仍不禁黯然。

饒公最感到遺憾的是10年前有一段時間患了中風,如果不是這樣,他表示還可以多做些學問,「我希望保持身體健康,盡我的力量為國家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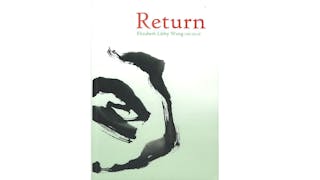
小小年紀的錢其濂和她的家人,他鄉當作故鄉,紥根香江,重新出發。不怨天尤人,但對人文情懷和傳統道德有所執着,反映了前輩們面對生活轉折從容應對的態度。

灼見名家傳媒對教育內容的重視,保持我對教育的初心,論對教育的重視,我敢說沒有其他媒體可以相比。這條路不容易走,但有很多支持者和讀者,給我們鼓勵與打氣。

張翔教授與港大校友見面時,提到港大要與本地社群連結,發揮社會影響力,也要向多方爭取資源拓展研究項目,以此回應時代和大學教與學面臨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