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香梅女士:「在華府政界打拼,驚濤駭浪。政客們無非是籌錢、拿選票、做高官。我口袋有錢,手中有筆,無求於人,做人講良心,做事講原則,才保平安。」

在整個「反英抗暴」鬥爭中,父親實際上都是站在「第一線」。他本來主要負責晚報的工作,即白天上班晚上下班。而負責《大公報》的同事,特別是要聞科等同事要在凌晨大樣定了後才可以下班,所以晚上上班。

羅孚先生是公認的伯樂,不少文化界的名家都與他的發現和培育是分不開的。這些響噹噹的名字,包括了金庸、梁羽生、董橋、李怡等等。

四人相見,心中愉悅之情難以形容,都已是頭髮斑白長者,都經歷了人世間的滄桑變化,所以這次甲子重聚,我們四人既感歡樂,心中也不免有絲絲感慨。60多年的前塵往事,短短幾小時怎傾訴得完。

金庸畢生從事文藝事業,成為影響幾代華人文化的作家和報人。〈惟其是脆嫩〉中慷慨激昂的言詞,亦必然令他深受牽動,而其後他亦徹徹底底地用小說作品回應了林徽因的託付了。

從廣州的惠吉西二坊二號,到倫敦的唐寧街10號,羅海星和我走過的人生路,究竟有多麼漫長,多麼曲折,多麼艱辛,實在是無可估量的!

《蘋果日報》前主筆之一馮偉光(筆名盧峯),昨晚10時左右在本港機場準備離境時被截停拘捕。另《立場新聞》昨晚發公告稱,為減低各方風險,決定將今年5月份及之前刊出的相關評論文章暫時下架,並停止接受贊助。

德國記者保羅.戈德曼(Paul Goldmann)所寫的《一個中國的夏日》德文版於1898年出版,因為種種原因,作者和他這本着作似乎被遺忘,直到一個世紀之後,一位國王湖小鎮上的華僑無意中發現了這本書。

香港早年報紙的「三及第」書寫文體,混合了文言文、白話文及粵語,別具一格。50-60年代,作家三蘇把香港三及第文化發揮得淋漓盡致;他憑着生花妙筆馳騁於左、中、右派報章之間,左右逢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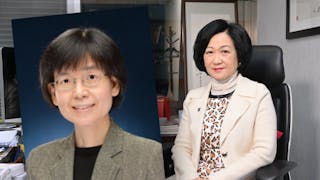
在中央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新時代,公務員體制或個人,尤其是政務官,恐怕難以獨善其身。

《大公報》與費明儀,固然源自她的二叔、前社長費彝民先生。大概不太多人知道,費明儀曾一度擔任《大公報》記者,採訪來港演出的傳奇女高音周小燕。

老曹一生都奉獻給了《大公報》,一張旗幟鮮明的愛國報紙。他一生磊落光明、待人誠懇,不斷追求知識,克盡報人責任,樂於提攜後輩,大公人不會忘記他。

老曹等前輩經常教導我們,處理新聞,要有自己見解和看法,如果人云亦云,那是很難有競爭力的。

有權力的人,想像力是無限的,可以想很多罪行。雖則香港人在香港犯事在香港審判,但大家回想張子強在香港犯事,風水師在香港殺了人,都在內地審訊和被處決。余若薇已經批評這做法不妥,有違原則。

歷史的發展,雖然有必然性,卻往往帶有偶然性;金庸的一生,交織着必然與偶然。

今天媒體生態跟幾十年前完全不同,再過幾十年報紙的面目如何都未可知,但新聞卻是永遠存在的。面對全球資本集中和壟斷的情勢,如何保持言論獨立,良心泰然?我們必須思考,也是紀念張季鸞和《大公報》的意義所在。

《大公報》代表中國士大夫階層向現代知識分子角色轉型的過程。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以後,知識人的角色愈來愈邊緣化,而報刊是知識人重新進入政治舞台的一個重要途徑。

以前的小報性知識信箱,很多來信都是報館中人向壁虛構,當然也會有所謂「心急人」寫信到報館,請教一些生理和心理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