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海進入龍津道時回頭看看身後的西頭村,高高低低、斑斑駁駁的木屋群之間點綴着深紅、淺紅的簕杜鵑花,還有4月應約而來的木棉花。溫海聽見花兒說:「進去吧、進去吧!」

古希臘有三大柱式,科林斯柱是其中的一個柱式,柱頭在漩渦形之下再加上裝滿卷曲的茛苕草的花籃,雅典神廟的柱式就是這一種。

我看過許多死亡個案,也曾在死亡邊緣徘徊。年過60之後,經常猜想,會在什麼場景之下告別人生舞台。溫海的告別場景,也是我其中一個猜想,既然以小說面貌呈現,也少不了許多文學潤筆。

台灣中天新聞台誕生於台灣戒嚴時代解除之後,作為香港文化商人于品海在其「全球華人文化圈」中布局的一部分,一度發展壯大,被譽為「華人的CNN」,然而其後又無法避免地走向沒落。

從金庸的理論和報業管理實踐來看,與其說金庸是「文人辦報」,倒不如說金庸是「儒商辦報」,更為貼切。

歷史的發展,雖然有必然性,卻往往帶有偶然性;金庸的一生,交織着必然與偶然。

由於過去的史實不能無縫的與當下的時局配合,執政者就會把歷史事件改編成歷史故事以配合政治需要,久而久之,歷史故事成了群眾的「記憶」。

遙想錢鍾書曾在牛津Exerter College 苦讀,這學院與閣樓相距不出15分鐘步行路程,時間上卻相差了80多年……

塔吉克是中亞五國當中最窮的國家,人均收入一年1,045美元,早兩年到訪的旅客說從邊境小境去首都杜尚別Dushanbe道路難行,要兩個多小時才到首都,誰料到現在汽車走的是一級公路,四平八穩,半小時就到了,小王說這條公路是由中國政府協助新修建的。

穆罕默多夫去年突然病逝,官方報道語焉不詳,如果權力不能順利交接,恐怕國內茍安的局面又成流水。

總統辦公的宏偉建築,雪白的大理石在陽光下令人不能直視,美國總統的白宮,那有如此氣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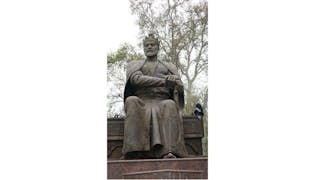
帖木兒是在東征中國途中逝世,遺願要安葬故鄉,即今天的沙克里什斯城。可是歸葬途中是冬天,遇上大風雪,改而葬在撒馬爾罕。

金庸說過,時局總是向着人們主觀的方向發展,所以不妨多一點向好的方向想,看時局看得樂觀一點,這樣時勢也許就會由壞變好。年輕時不解金庸這番玄話,年事漸長,愈覺得有道理,也就與讀者分享。

香港商人是不是也有粟特人的基因?

粟特人無權無勢,從來沒有組建成強大的帝國,為何能夠掌控絲路貿易幾近1,200年?

撒馬爾罕市集上向旅客兜售的麵包「饢」,五彩繽紛,抓人眼目;家庭日常食用的饢,圓圓的一個大餅,簡單的圖案,非常平實,稍為加熱,香口又有韌度,口感很好,是絲路上的主食,配上烤肉和羊肉湯,更是絲路上的美饌。

汽車離開邊防區駛向撒馬爾罕,日落金黃的太陽在車後映得滿天紅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