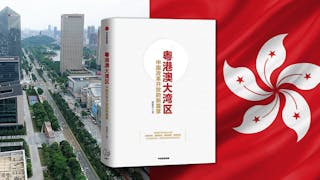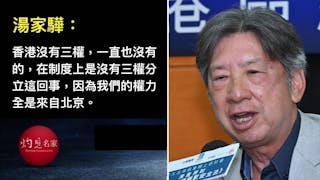
三權分立,我覺得香港的教育局要把這個課題刪除,因為政治不正確。香港並不是一個獨立政體,互相制衡、司法獨立對香港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維持一國兩制相信仍是兩地主流共識,但應承認,維持其背後1980年代的假設不變,已不再現實。

陳弘毅不認為中央單方面收緊香港政策,而是我方每走一步令對方不滿,於是對方走一步令我方不滿,情況愈來愈差,形成惡性循環。我們需要思考怎樣跳出這個惡性循環,從協商解決問題。

練乙錚認為香港2047問題國際化解決方式,就是採用瑞士模式,否則內部解決的可能性和代價可能很嚴重,或會爆發一場勝負難以預估的內戰。今次「反送中」事件看到的矛盾衝突,足以構成一次內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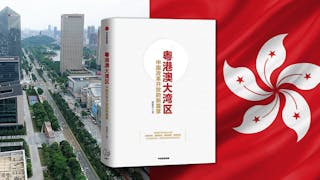
張思平認為,在經濟內地化的同時,香港也逐步向內地的體制和政策靠攏,甚至在政治領域,可能以消除「港獨」為理由,對基本法確定的中央和香港的特殊政治體制和政治安排做出一些重大調整。

思考香港之前途,要清晰了解和支持香港在21世紀的新定位,即作為非常成功和高效能的「中國之世界城市」。

像多數其他香港人一樣,我知道林鄭會避談政改這種令人不快的議題,一如她去年發表首份《施政報告》時那樣。不過,除了政改外,有些議題她亦從未觸及,然而特區政府和北京領導人卻遲早都要面對這些問題。

中文繁簡之爭,既是認知問題,也是使用問題。若果說,簡體字易學,對不是以中文為主要學習語言的學生來說,捨繁就簡會有較強的說服力。但在理由上加上2047這因素,就把問題複雜化了。

當年回歸談判期間,香港人理解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是香港可協助國家現代化,作用獨特且無可替代,因此北京願意容忍差異,並給予香港在基本法下50年不變特殊地位。

近期很多人談論2047年,但其實我們連由現在到2022年將會有些什麼轉變也不太清楚。

中共人士不斷重覆這個說法,特區有沒有一個官員出來維護我們一國兩制應得的高度自治權?

可惜還有很多港人未明白這些變化如何影響他們和下一代,或者我們要更努力喚醒這群人士。

民主自決是一種權利,1997年,為什麼香港人不能自決自己的命運呢?

如果緊張的關係繼續,我們無法基於互信精神,達成一個解決上述和其他問題的共識,那如何讓一國兩制走下去?

林太必須勇敢地擔負起重啟政改這項艱巨的任務,否則政府管治的質素只會繼續下降。

「唯民是保,是從民生出發,讓社會大眾重拾希望。」這是馬墉傑對政府新班子的建言。

父母、教育者是看2037、2047、甚至2057。當我們不在的時候,我們交付了什麼給我們的年青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