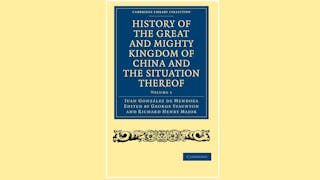「我一生與詩結了不解緣,讀書、研究、教學、翻譯都集中在詩。」張曼儀如是說。翻譯過程讓張曼儀如像重歷了卞之琳的詩歌創作過程,對他的認識又加深了一層。

余光中作品中不忌諱死亡,他表示不怕死亡。不怕死亡,當然也就不懼年老,不懼白髮了。然而,余光中真的不懼死亡嗎?人真的不懼死亡嗎?

我讀書十幾年,從未遇上過一個這麼認真的老師——他的中文字一點不潦草,整齊清晰之外,連微小的語文錯誤都細細糾正了,這樣批改一個作業要花上多少時間啊?

我覺得圖書館是一個繽紛世界,是濃縮的人生。人們在這兒大可以歡呼雀躍、感動流淚,更何況是通電話?看書,未必是正襟危坐、一本正經才能入腦的。

聞家和高家可說是門當戶對。外祖父非常喜歡父親,在和聞家的交往中,早就看上了這個孩子的聰明才智,回家來總誇獎他,特別是誇他文章和字寫得好。

要保持文學的獨立性,只要不是直接批評政府、直接批評政治,政府也不管你的。當時還有有限的空間,有限的自由。

白先勇教授認為,「五四」以來,中國為了救亡圖存,全面倡導西式教育,以致中國傳統日漸式微,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幾乎沒有發言權。時至今日,中華民族自我救贖的方式,應該是重回傳統、發起一場新的文藝復興。

少年毛澤東中途輟學,到田裏勞動,但他勤力學習,晚上會偷偷閱讀。有一本書,毛澤東閱讀後,改寫了他的人生。

「我們了解過去是如何想像出來的,可以幫助我們想像今天,並且想像將來。」

我們留不住時間,但我們能守護屬於自己的記憶。記憶可以盛載着我們成長的花絮,也盛載着昔日的恩情,還盛載着對這塊土地的熱愛。

《圍城》是一部非常難得的作品,是「癡」、「笑」、「博」和「悲」的結集,現在想來,難出其右。

後來武俠小說愛寫異人,棲身僕役,恐怕多受《崑崙奴》影響。

國文的根基愈好,看古書的能力愈強,愈能體會到做一個中國人的驕傲。

那男子又在口中吐出一個二十餘歲的女子來,兩人一起對飲調笑嬉玩。

當電影、舞刀、話劇都是創作形式的時候,戲曲為甚麼不可以呢?

李娃嫁入鄭家,治家甚嚴,持孝至甚。後鄭生父母皆歿,鄭生守孝畢,遷任刺史,李娃封汧國夫人。

白先勇道:「現在是時候讓我們對這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對中華文明作一個客觀、全面的re-evaluation(重新評估)。」

結合雅俗並存的文辭、寬容的胸襟和嚴謹的架構來書寫屬於一個民族的時代和故事,更是一個民族的心理投射。

這些社會百態若沒有透過小說去濃縮,人一生哪有那麼多時間去體驗?

《李娃傳》寫唐代書生愛情遭遇,曲折多變,寫出人間嗔怨,世道滄桑。

西班牙人遇到中國人時,他們意識到自己沒有什麼可以提供給中國人的,甚至整個歐洲裏也沒有人能夠提供中國人什麼。後來他們意識到有樣東西是中國人喜歡的,那就是銀。

文社運動的盛衰,原因千絲萬縷,不只是一篇文章,一篇評論可以影響得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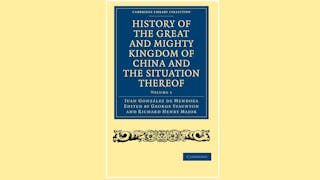
《中華大帝國史》在1585年出版,是當時唯一有關中國的資訊來源,它對於中國的看法相當正面,後來被翻譯成多種歐洲語言,亦在100年間不斷再版。令人驚嘆的是,為什麼它會完全被遺忘呢?

何以林妹妹奔喪回來突然就寄人籬下,一無所有了?

16世紀的歐洲人,特別是葡萄牙人,是為了什麼來到亞洲呢?不是為了中國的領土,而是為了香料。如果不是意外與中國接觸,中國對於他們也沒那麼重要。

六七暴動之後,已很難招收社員了,幾個因素加起來,包括你所說的報刊轉變方針,文社可以發表的園地便日漸萎縮。

我是如何接觸到現代的呢?主要是從報刊上看到當時「座標現代文學社」的文章而來。該社是草川、尚木、蘆荻等辦的。

只要我們能夠睜眼正視歷史上確曾存在的苦難,我們就能成為勇者。

文學是他的宗教,相信他會一直背着復興中華文化的十字架走下去。

孫恪正茫然不知所措的時候,只見妻了的衣衫裂開,向着剛才叫嘯的猴群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