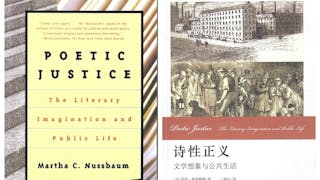小說《In Situ隱山之人》表面上沒有人死亡,底層觸及的,卻是100%死亡的物種滅絶,比死還可怕。

香港早年在粵劇方面比廣州原本保留更多例戲,更有破例立新的膽色,採用小提琴作頭架是薛覺先的實驗。這份mix and match的膽識和創意,是地道香港人素常出現的改革意志。

論到香港文學的價值在哪裏,她與香港歷史和社會現實構成怎樣弔詭的關係,足證文學的多元價值,香港的本土文學,既可作跨域理解,為香港人說故事,為香港編寫歷史。

評論可以同時間溝通創作者、作品、觀眾/讀者,互動中它又逕自延展,時而奪目,時而隱約,時而靜默,時而劃破世紀的暗黑。

有郊野公園告示這樣寫:「請將攜來垃圾帶走」。誰會把垃圾攜來攜去呢?漢語邏輯講求會意,不必事無大小都添加說明,用英文來思考。

「六十年代裏你最滿意哪首詩作?哪首是代表作?」「我認為我目前寫的詩更好。」「換言之,今天的你打倒昨日的你?」「是,永遠刷新,明日打倒今日的我。」

草川自小喜愛古文,接觸文言文,發現可以借古文入現代詩,自言其新詩創作說不上反叛,但父親是古文主義者而自己則是現代主義者,父子不免為此爭拗。

文社運動的盛衰,原因千絲萬縷,不只是一篇文章,一篇評論可以影響得到的。

六七暴動之後,已很難招收社員了,幾個因素加起來,包括你所說的報刊轉變方針,文社可以發表的園地便日漸萎縮。

我是如何接觸到現代的呢?主要是從報刊上看到當時「座標現代文學社」的文章而來。該社是草川、尚木、蘆荻等辦的。

那帶弧度的廣角鏡頭下被青巒環繞的清澈湖泊,怎能脫掉「執意保留傳統終被自然淘汰,人類超越生死的情才會穿越文獻歷史而重生」這隱喻。

「你的歌聲很好聽」,唯獨那一刻是女性的話,其他時候主角是喪失性向的身體,猶豫在森林以外,直至遇上安珍卓尼,她變成第三者──既非自己亦非他人。

Bob Dylan 和 Beat Generation 用詩歌來beat那關在鐵屋子的generation,我們呢?我們憑甚麼敲醒這一代?

陳冠中在公開講座再提「一種華文,各自表述」的觀念,在去年10月29日香港浸會大學的「地域與文學」中的六方對話他也曾提出。唯這近年不斷論述的觀點,如何反映他在本土文化建構成形中的文學觀照?

V城的百年演變下的董姓家庭如何塑造一個宅在高樓的文字工場想像和創作的人,側映香港這小城不得不由書延伸,展開繁史的可能,而扭曲不但指軀體,還包括歷史──屬於香港的百年扭曲,歷史扭曲,成長扭曲,性別扭曲。董在《地圖集》說虛構是城市的本質,自我擴充,修改,掩飾,推翻,似乎為這種通過巧飾的想像和創造,對抗過份唯物寫實的自然觀和創作觀,抵禦人性的扭曲和物化的思想提供了暗示。

完場時編劇兼導演陳敢權表示:編劇家操控角色的命運,卻操控不到自己的命運;他為劇本中的人物表達深情,卻在現實中無法對所愛的人表達深情;劇場上的創作揮灑自如,卻無能力處理生活。

當我們的視野只餘岸堤/熒煌的燭光映射著梔子燈/龍笛觱篥小唱笙歌/歌聲不及纖纖玉指中的新橙甜/情愫比不上錦幄枕角下的才子

虞美人 如果當天,你還是一個小孩 把蓮花飄送在河上許願只是 挑撥幾下的心弦 我艷紅的夢會不會像留在汴河上的小舟 早已回到沉落的京城 雕鑿的亭台樓閣,閃劃過的華蓮 委曲把回憶唱給城市的新人類聽 歷史不斷重演 誰知今天奪得江山的 子孫終也敗在 太喜愛春花秋月的風騷 世代轉移 拆掉區隔的高牆 開敞沿街叫賣的商戶 讓住在後頭的貴族小姐 盡情消費 馬行街前的 坐在小轎內的姑娘 偷拉布簾張望 一江清明的春水 依然向東流 青玉案 巨富官商招遙在會仙樓 正店點燈 把銀盤屈卮照耀通明 市井攤販擾攘到三更 御街前有人表演雜技有人吞火 有人鬥鷄有人耍猴 有人提線連綴木偶說故事 勾欄瓦肆 愈夜愈美麗 打過四鼓才歇息 五更又熱情地開張 怎會關心 我們的愛情 能否恰似 上元節大街上連續五晚放綵張揚的 車馬龍舞與流光的花千樹? 孤寂漂泊的白衣少年 手持的紅燈 只有我明瞭 像郁達夫沉醉在東風裏不願醒 試場失意前途戛止 誰會在意 那震懾的釵鈿盪漾的雪柳 雲鬢浮過的笑靨 迎迎在車水馬龍的轉動中 等你 千年以後的驀然紙間 […]

讀這部少女寫的書,可以充分想像,她如何為了尋覓野花而瘋狂地忘我……

只可惜詩人沒有這樣循這條路徑走下去,卻斗入因文革而產生的激憤和焦慮,使他無法再詩也無法自拔,好像「一個消息背後/恒常是最深沉的遞變」。

只可惜詩人沒有這樣循這條路徑走下去,卻斗入因文革而產生的激憤和焦慮,使他無法再詩也無法自拔,好像「一個消息背後/恒常是最深沉的遞變」。

我個人堅持叫他始初傳入香港時的譯名——叮噹。事實上,當時除了大雄的名字一直維持外,胖虎(曾譯成技安)本來叫肥仔,小夫(曾譯阿福)本來叫牙擦仔,名字地道且入屋入型入格,使小孩讀者沒有文化隔閡,造就他引入香港不久旋即有電視台買來播放。

高行健的長詩曾引來一位在台灣教書的大學老師劉正偉的不滿。他認為高行健詩集中這首「主打詩」大多是詞組、片語或成語的堆疊、拼貼,若不召開記者會做新書發表會,又或者姑隱作者其名,初讀者可能會以為是中學生初習的拼貼作品,了無新意。把他詩句分行去掉,就像一段平凡庸俗的散文。

在骷髏野地哭喪的臉孔,呼叫,加上蒼蠅亂飛的聲音,破落的殘破磚瓦,構成象徵死亡的畫面,催促復興文明的迫切。另一較容易引起關注的,是最後晚餐的再造畫面:耶穌已不再是最後晚餐的主角,耶穌門徒荒誕地變成賭徒,彈指之間,灰飛煙滅。寓意宗教也不能拯救人類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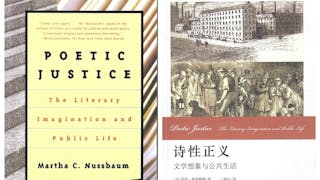
在這語言貧乏,溝通能力薄弱的世代,詩是城市的呼吸,靈魂的窗口。真正的詩人之所以能夠沒有溝通的包袱,仍因為他知道人類對自己所設計的語言常常基於個人認知的限制而失焦滑落,詩用異於言表的震撼叫人解除只圖尋求溝通表層的疏懶,而要省思不同思想體系的關注。

語言表達有所謂三成來自文字或聲音符號,七成來自態勢語。語言又分外在語言及內在語言,演員沉默時,不代表沒有劇本存在,其行動是一種內在語言。而大部分時候,人類的內在語言卻往往是真實及最具涵量的。於是我想:這場舞劇,展示了劇場的詩性想像的可能。

1944年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收入她第一本小說集《傳奇》,翌年馬上親自改編成劇本,在上海蘭心劇院公演40多場,盛況一時無兩,突顯文學與劇場的互動光輝。香港文學與劇場這對孿生兄弟何時相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