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李活道的名稱,顯然帶有不少神秘色彩。不但對於所欲紀念者到底是何許人所知不多,就連以此命名所欲何事亦知之有限。坊間更不乏按字面推斷之說,甚至指是因當年該處生長了不少冬青樹(Holly)之故。

孫中山當年往返於中港澳三地之間,這些史事和史蹟都是互有關連的。時至今日,澳門有不少地方留下孫中山當年活動的史蹟。

上星期還在聽「香港書神」許定銘講早年到旺角覓書的故事,當時我們不約而同提到德仁書院牆邊這個書攤,幾天後我就從藏家那裏收到這張老照片,真是有緣!

洪承疇降清主要原因非莊妃獻身,而是深思熟慮後認為投降可以再展抱負。兼且兵敗被俘,即使逃回明朝,面對刻薄寡恩,喜怒無常的崇禎帝,會有什麼好事呢?

1943年前,傅秉常長時間在立法院和外交界服務。傅秉常與伍朝樞、孫科關係尤深,一生仕途起伏進退,亦多與兩人有關,故本書討論伍朝樞和孫科亦較詳細。

論者一般甚少談到傅秉常與香港的種種關係,而這一部分卻是傅秉常研究的重要一環。本書嘗試根據各種原始資料,填補這一缺門。

筆者希望透過這部傳記,探討傅秉常這位具香港背景的粵籍社會精英,如何參與中國近代化的進程,由此反映香港在中國近代化中所擔當的角色。

當年念近代史,「九·一八」事變已如烙印般,鑴刻心中。想不到,多年後,竟然有機會來到瀋陽,踏足在這個地方。

洪承疇(1593 – 1665)是明末清初的大漢奸,也是建立清朝的大功臣。幾百年來已成定論,但很少人留意到滿州人的覆滅,早在洪承疇的計算中。

《時務報》的重要性,不單只開啟新思想新風氣,更領導其進一步發展,而匯成維新運的熱潮。

水月宮經歷過兩次重修,破壞了原來一些特色,2010年獲古諮會確定為三級歷史建築。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中,實居於一個新時代的啟蒙者的地位,其思想學術的價值在其開闢門徑,及其所予人的啟發和影響。

今天的中國還不是一個智力構建很堅實的現代大國。我們固然想要培養大量能夠創新和創價的人才,但是往往「有心栽花花不發」。

張亮認為,欣賞藝術不一定穿西裝打領帶,正襟危坐;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藝術表演方場地,而大館正為藝術走入民間而努力。

《時務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一年丙申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報採旬刊形式,逢初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每冊20餘頁,約3萬字,用連史紙石印,頗清晰美觀,自此成為維新派的正式言論機關。

羅香林認為,研究是一個生命,由內到外,由近至遠,一一分析。香港的名稱由來,乃至石排灣、張保仔、魔鬼山、大埔等等,這些地方的故事和歷史,都由羅香林一一補白。

從小,教科書一直強調,香港開埠以前是一條不知名的小漁村,這大概是我們集體回憶裏完全相同的標準考試答案。然而,若只是小漁村,為何數百年間西方國家一再嘗試攻佔香港不同地域?

向後看的目的是為了向前看。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這正是我出版這本書的初衷和願望。

法國政府去年在70號山頭豎立紀念碑紀念加拿大陣亡將士,名單之中第一次出現華人姓氏,引起各方好奇。經過一番努力,終於確定Frederick Lee是加拿大華人Chong Lee的兒子。

後起的現代大國是美國,在歐亞大陸之外。除了十九世紀末從西班牙手中接管了菲律賓之外,沒有在「東方」參與過殖民地的爭奪。

正所謂「兵不厭詐」,我們不難為信玄瞞着所有人找到可行的理由,例如有戰略的考慮等等,但這裏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想想:其實信玄並不想立即與信長為敵。

西方朋友對中華文化的欣賞,有時候反比我們更懂更深入,不禁讓人汗顏,是時候多花時間發掘自己的寶庫了。

早年東華的籌款方式主要是總理捐獻和沿門勸捐,後來籌款活動五花八門。為配合東華三院邁向150年的大日子,東華三院即日起至明年3月底展開「籌募文物」徵集計劃,邀請市民捐贈與東華三院籌募活動有關的文物珍藏。

自從有了現代科學技術以後,我們所謂的現代大國的影響力,就不再是算術級數的增加,而是幾何級數的增加。

假設沒有新界,港九只是個彈丸之地,天然資源有限,發展空間受制,很難獨立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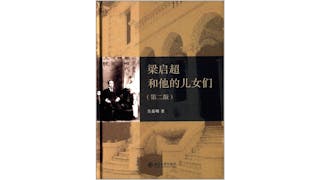
家族史是近年新興的研究範疇,梁啟超家族人物眾多,各具特色,有的還可獨立出來成為進一步探討的對象。

丁新豹:「很多人以為特區政府沒有重視保育舊建築,其實拆卸舊建築最多是上世紀80、90年代。」

香港真是歷史處處,很多地方都頗值得遊覽。西貢與大嶼山東涌有很多宋代的歷史足跡。

惠特之演說及簡介中國女哲人,我們其實大都可以同樣廣查資料;聆聽之際感到欣賞,其實也在怪責自己素常忽略了中國的「女諸生」。

《策展革命: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啟示》一書探究了博物館展覽與政治運動的關聯,分析了政府如何使用展覽達至政治合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