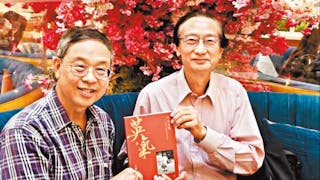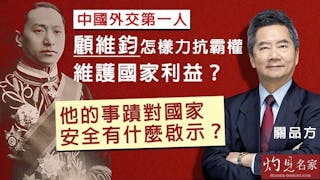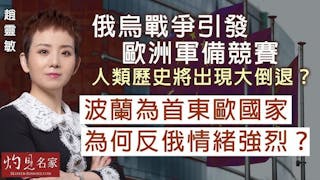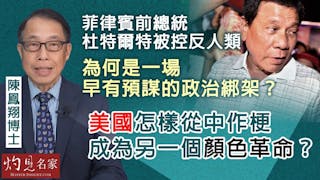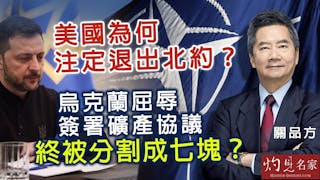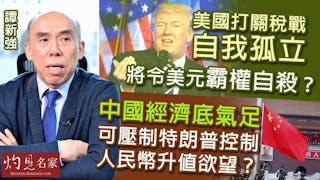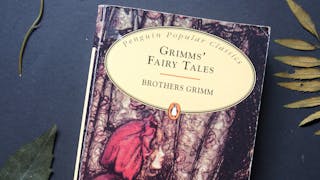近年來,STEAM教育如雨後春筍,在不同的領域都能見到科技的應用。現時,沉浸式科技如AR(擴充實境)、VR(虛擬實境)等技術層出不窮,為文化教育帶來更多可能。究竟如何才能真正利用好科技的力量,不讓科技成為一種裝飾呢?
筆者與同事趙振洲博士早前獲得香港教育大學的資助,進行大灣區非物質文化遺產虛擬博物館互動平台開發先導計劃(客家文化篇),聚焦港深二地的客家文化,嘗試用科技聯乘文化,推行非遺教育。
計劃的簡介和執行
非物質文化遺產除了富有歷史、文化和社會意義外,也富含着教育意義(註) 。客家遺址作為承載客家文化的自然空間,極具開發潛力。為了讓同學在互動、自主與不受限的虛擬空間中認識非遺和客家文化,研究團隊決定將文化遺址數字化,轉化為線上客家文化教育平台。
我們夥同教大文化傳承教育與藝術管理榮譽文學士課程的學生,一同進行這個先導計劃。四年級學生李依晴的參與度很高,除了在研究團隊協助下完成了虛擬博物館的教材套設計,包括撰寫考察地點的背景調查、實地拍攝720全景圖片、視頻製作和平台綜合設計等,更舉辦了兩次實驗活動,收集了不少珍貴的數據。

文化真實性與技術創新性的平衡
虛擬博物館其中一個重點是要平衡「文化真實性」與「技術創新性」。確保文化真實性最重要的是內容的設計。李依晴表示:「研究團隊根據收集的學術資料進行教育導向的創作,以求最大限度地保留文化真實性,利用技術創新賦予內容娛樂和教育意義。」
曾大屋的教學活動,研究團隊會請參與者閲讀族譜原本節選,以識別建造者曾貫萬的人生經歷,從而理解建築的資金來源和歷史背景。這種方法不僅帶給觀眾參與研究的體驗,培養分析與判斷能力,還增強了文化真實性。內容設置了住在曾大屋的客家老人──曾嘉英這個虛擬角色,由她帶領觀眾參觀元宵節的點燈儀式,這是非遺的生動演繹,以貼合觀眾生活的角度,導入知識和價值觀。
筆者在審閱先導計劃的研究數據,發現了學生知識吸收率在實驗後平均提高了45%,對客家精神的認同感也能達到平均70%。
客家文化和非遺的深度嵌入
本計劃選取了多個類型的香港、深圳文化空間,同時也給資料整合和內容開發帶來了挑戰。李同學說:「一開始研究團隊也試圖找出一個統一的規則嵌入內容,後來發現曾大屋是圍屋、孟公屋的取景是祠堂、上窰民俗文物館是布置好展品的博物館......經過討論,研究團隊靈機一動,這些空間正好互相補足,形成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的客家文化印象。」
如此一來,研究團隊正好在不同的虛擬的文化遺址上,建構不同內容,做到互相補足、互相配合。
註:
劉芳(2018):〈博物館教育與學校教育的整合與利用問題研究〉,載於《科教導刊》,(6),頁178-185。
宋向光(2015):〈博物館教育的新趨勢〉,載於《中國博物館》,(1),頁1-5。
Delgado-Algarra, E. J., & Cuenca-López, J. M. (2020). Challeng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identities with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Heritage education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Delgado-Algarra, E. J., & Cuenca-López, J. M.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citizenship and heritage education (pp. 1-25). IGI Global.
Santisteban, A., Pagès, J., & Bravo, L. (2018). History education and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In Davies, I., & Ho, L. C.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global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pp. 457-472). Springer 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