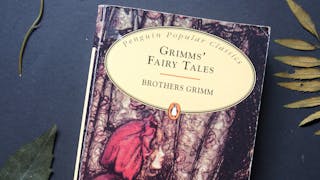3月27日是英國政壇相當重要的一天。就在這天,胡姆扎·尤薩夫(Humza Yousaf)接替施雅晴(Nicola Sturgeon),成為蘇格蘭民族黨新任領袖暨新任首席大臣。他是蘇格蘭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首席大臣,以及首位領導英國主要政黨的穆斯林。
在獲勝演講中,尤薩夫談到60年代從巴基斯坦移民到英國的祖父母時,如此説道:「作為移民,他們曾經幾乎一個英語單詞都不會,他們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自己的孫子有一天會成為蘇格蘭的首席大臣。」
是的,這在20年前,不要說來自遠東的巴基斯坦人或印度人,就算是英國人也不會想到,自己國家的重要職位,竟然會由有色人種擔任,包括首相。

時光倒流1000年
如果時光倒流,來到1931年的英國,那時甘地正在倫敦參加有關印度前途的圓桌會議。相片中他身穿印度傳統服裝,一臉堅定且平和,身邊圍觀的都是白皮膚的英國人。他們也從未想過,不用一個世紀,一位同是來自南亞的印度人,會領導這個曾經白人至上的國家。

如果將眼光拉到1000年前,那時正是十字軍東征的狂熱時期。在這9次表面朝聖,實質掠奪;表面救贖,實質摧毀的征戰中,英國的「獅心王」理查也從未想過,自己的國家將來會被那些視為邪惡的伊斯蘭人所領導。
當然,這個所謂的「邪惡」,其中既有教皇的蠱動和野心,也有貴族的貪婪和權謀,更有無數下層人民的宗教狂熱和投機之心。政治、經濟和宗教糅合在一起,造成了多少生靈塗炭,無可逆轉的破壞。(故此「十字軍東征」[Crusade]的翻譯很有問題,因為這個橫跨200年的殘酷征戰,理想成分少得可憐,盤算和交易卻如此的赤裸裸。)

更值得提的是,當時被妖魔化的伊斯蘭文明,無論在文化內涵和科學技術上,均遙遙領先歐洲各國,他們的領袖薩拉丁(Saladin)的宏圖偉略和寬宏大度,也令那些蒙上帝恩寵的歐洲貴族所折服,稱其「具騎士風度的君主」,著名的大主教和編年史家提爾的威廉(William of Tyre)更認為他是「睿智、勇敢、慷慨無比」。

仍具市場的十字軍意識形態
1000多年後,同是來自穆斯林/印度的有色人種,成為舉足輕重的現代英國政治人物,穆斯林族裔在英國政壇的影響力與日劇增,這說明了什麽?
這説明了向來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規範,已產生巨大變化,人類正在面對一場無與倫比,影響深遠的千古變局。故此,即使是擁有1000多年民族歷史和基督信仰,以盎格魯─撒克遜民族文化傳統為自傲的英國公民,也需要正視現實,放下身段,投下重要的一票。
有趣的是,西方為優、白人至上的意識形態,在西方已開始轉變,但在香港這個遠東小島,卻依然極具市場,某類中國人依然致力擁護意識形態上的十字軍東征──西方白人的見識就是高人一等,需要肅然起敬;西方的社科理論更具普遍性和科學性,是「國際化」的指標,所以要亦步亦趨;西方人的讚揚和稱許,就是臉上貼金,更是權威來源。
西方的一切,都是如此美好,猶如油畫中的伊甸果園,雖然裏面從來沒有出現過東方面孔。
是的,自清末以來,中國人該如何為自身定位,如何不卑不亢,如何看清時勢,與時並進,真是不容易。這對於身處香港的某些中國人來説,則更為困難。有研究者認為,「港人在自身定位方面從來都沒有經驗,無論是政黨還是普通市民,都不清楚香港在複雜的全球性政治上應如何定位。」(張炳良,2021)
為何如此?
歸根究柢,還是與文化土壤密切相關。我們長年缺乏文化根基和歷史教育,且不以為恥,更引以為榮。故此,香港人的定位往往在鐘擺兩極來回晃蕩,或是虛無空泛的世界公民,或是狹隘排外的本土立場,諸多光怪陸離的現象從此而起。例如在國際學校任教的朋友告知,在諸多種族的學生(包括家長)中,對自己國家的文字最為自卑,且缺乏歸屬感的,就是香港人。
正常嗎?
看來我們真的需要惡補文化知識,例如多點了解十字軍東征的真實歷史,得知教宗和貴族們的真實面目。要不然很容易動不動就披上銹跡斑斑的鐵甲,踏上「征途」。雖然只不過是跟在隊伍最後揮旗呐喊的小嘍囉,卻自以為蒙主恩寵,自我感覺良好,殊不知人家隊伍的首領,早已換上了東方面孔的有色人種。
而時至今日,這個雜牌隊伍既是各懷鬼胎,也是方向茫然,且步步維艱,更早已被迫面對現實,偏離了當年十字軍東征的路線。
整個世界的布局,早已經不一樣了。
既然如此,又何必屁顛屁顛的跟在後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