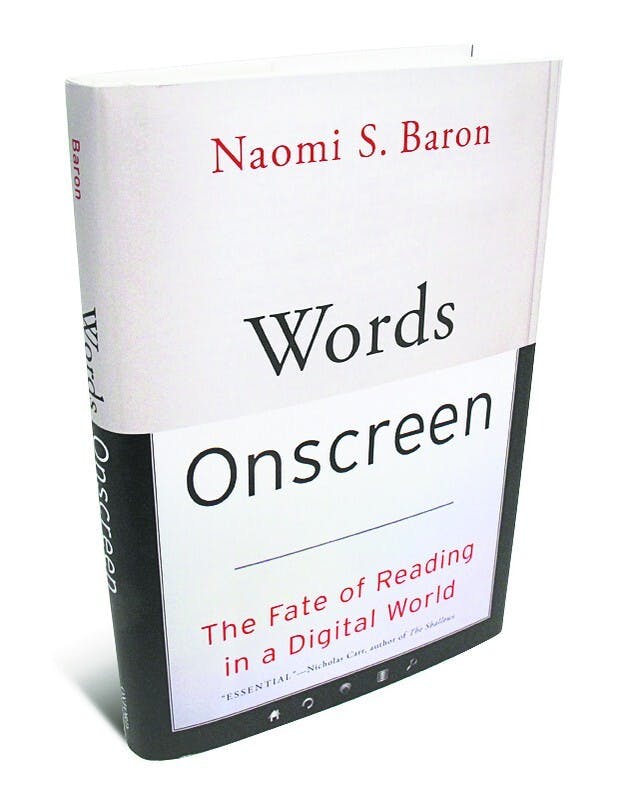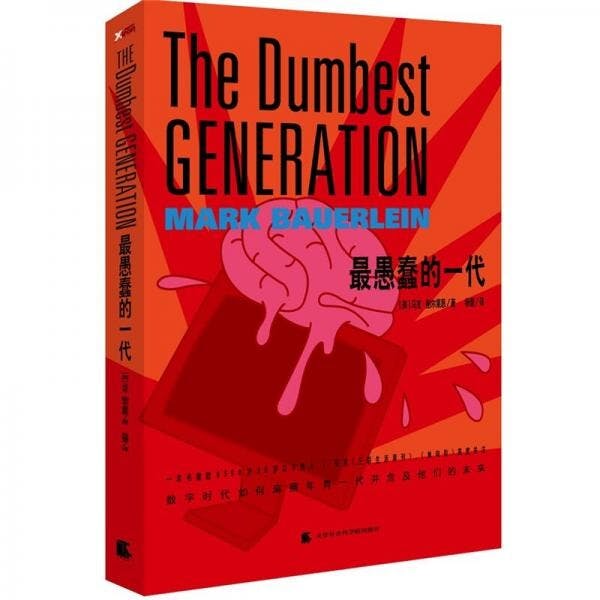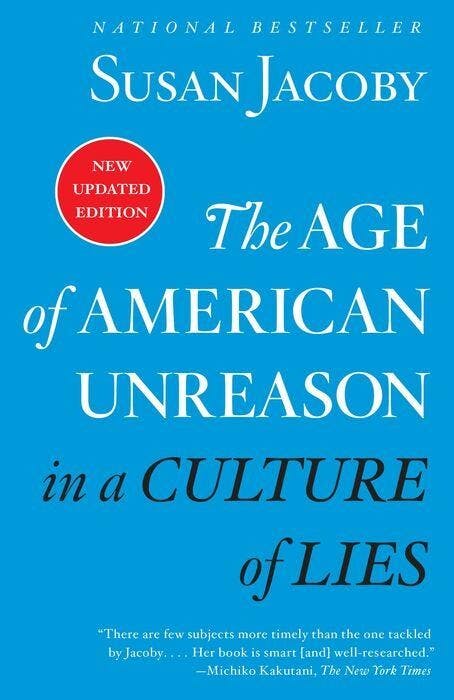古兆申先生過世後,他的老朋友整理了他近年的文章,打算編輯成書,其中一篇名為〈雨傘運動與手機世代〉的文章勾起了我的懷念和思考。該文寫於2014年,其時「雨傘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古先生對社交媒體和手機世代深有感觸,寫下此文。
重看這篇文章,令我聯想起社會運動時期,出現在臉書(Facebook)上的一幅油畫──《珍·葛雷的死刑》(The Execution of Lady Jane Grey)。透過對這幅油畫的理性分析,有助理解社交網絡之諸般弊端,以及盲從畫面的無知荒謬。如果言之成理,本文也可作為古先生鴻文的一個新註腳。
3年前社會運動最嚴峻之時,沈旭暉副教授在Facebook上貼出一幅油畫,畫作地點是500年前倫敦塔的一個地下室,正中是一位身穿純白衣裙的妙齡少女,雙眼被蒙,神情惶恐,正走上受刑台。手持斧頭的劊子手目無表情,一旁的女僕神情哀傷,偏過頭去,不忍卒視。青年導師將儈子手比擬為香港政府和警察,而那位悲慘少女,則代表了被政府逮捕和指控的青年們。該帖文一出,相當煽情,引來萬人熱烈留言,群情洶湧。

網絡時代,往往一張相片,一張油畫,甚至區區一個標題,就能泛起滔天巨浪,撥動情緒,左右「民意」。但最終我們還是要回到現實,認清真相。
這幅油畫說的是什麽呢?它描述的是16世紀中葉,發生在英國的一場充滿血腥的王位爭奪事件。英王亨利八世有二女一子,他去世後,將王位傳給年僅8歲的愛德華王子。愛德華自小多病,7年後就病逝了。在他死前,想將王位交給同樣宗教立場(聖公會)的二姐伊莉莎伯,以免落入信奉天主教的大姐瑪麗之手。但諸般限制下,他最終將王位交給了自己的童年玩伴──表妹珍妮(Lady Jane Grey)手上。
年僅15歲的珍妮毫無野心,性好讀書,而且剛剛新婚,卻無緣無故成了英國國王。
愛德華一死,野心勃勃的大姐瑪麗(即「血腥瑪麗」)發動政變,成功奪取權位。她將珍尼夫婦囚於倫敦塔,旋即以叛國罪予以斬頭死刑,其親人全被處決。珍妮由登基到被殺,不過短短9天,就成為無辜的政治犧牲品。珍妮之登位,是被幕後勢力捧上去的,包括想借此獨攬大權的攝政王諾森伯蘭公爵,更包括不諳世故,不懂政治為何物的表弟愛德華。這幅畫所描繪的,就是15歲的珍妮在倫敦塔被斬首的場景。
沈副教授的引用有何不妥呢?我們可以從歷史事實和創作背景兩方面去「解構」。
不符歷史事實的引用
首先,他將珍妮比擬為那些充滿理想,為「革命」抛頭顱、灑熱血的有為青年。但現實中珍妮卻是一個不懂世事,被無端捲入成人政治鬥爭的未成年少女,如此類比,毫不相關;此外,這並非由上至下的暴政欺壓事件,而是上層宮廷權力爭奪,並無平民被迫害的元素,青年導師將之類比於「暴政」政府,也是張冠李戴,亂扣帽子,用心相當險惡。
如果真要將壞人揪出,那些壞人就是該次政治鬥爭中的每一位成年人,包括利用珍妮的攝政王諾森伯蘭公爵和奪取權位的瑪麗公主,也包括那些不顧珍妮死活,見風使舵的王公大臣。就是這些人,把無辜無助的少女珍妮推向死亡深淵。這裏面並沒有熱血青年,只有身不由己,思想單純的無辜少女。故此,將該油畫來類比香港政局,毫無關聯,且極不妥當,但用來煽動情緒和挑起仇恨,卻絕對成功,無需成本。
無視創作背景的引用
珍妮死後300多年,法國畫家保羅·德拉羅什(Hippolyte-Paul Delaroche)創作了此畫,但他並非爲了重現歷史場景,而是刻意布局,希冀在沙龍比賽中獲獎,從而名利雙收。根據英國國家美術館(National Gallery)的專家研究,此畫有三大「創作」特徵:一,地點和場景不符歷史事實;二,内容迎合觀衆偏好;三,構圖和主題刻意撩起法國人對法國大革命的記憶,以冀達到「吸睛」效果。
不出所料,這幅精心布局的油畫在展出時極受歡迎,德拉羅什也爆得大名。但他死後,聲望迅速下降,輿論如此評價,「繪畫在他手中變成了說故事的工具,成爲文學的幽靈和傀儡」。
德拉羅什生前在事業上刻意布局,用心經營,卻沒有想到,自己的聲望在他死後會如此沉寂;他更沒想到,200年後在1萬公里外的東方小島,竟然有位香港「知音」利用自己的名作,挑起了煽情,鼓動了激憤,左右了判斷,雖然很多人連自己的名字也從未聽過。

古兆申的擔憂
古先生認爲,只有文字和閲讀,才能發揮頭腦中的想象力,帶領我們進入認真深入的思考。影像和圖片直白簡單,卻是支離破碎和相當片面,很容易弱化我們的理解與判斷力。可是在「雨傘運動」中,資訊科技所營造的虛擬力量,成爲這場運動的主要特色和動力,
「……煽情、造假、抹黑,變成此次運動最重要的手段。手機的方便與迅速,更把這類負面功能發揮到淋漓盡致:幾秒之間,假象變為事實、偏見變為正確、意識形態變為真理」。
「如果我們的青年人一直停留在『雨傘運動』這一批手機族的水平,香港的前景令人十分擔憂。」
4年後,香港爆發了那一場以年輕人爲生力軍,比雨傘運動規模更大,影響更深,直接影響香港前途及命運的社會運動。層出不窮的圖片和影像在網上肆意散發,不斷傳播,影響着人們的思維,包括這幅200年前的油畫。
盲信網絡、知識貧乏的新時代
美國語言學教授Naomi S. Baron的著作《數字世界中閱讀的命運》中,揭示了網絡世界對書寫的巨大衝擊,瀏覽代替了閲讀,從而降低了人類思維、反省和表達的能力;Mark Bauerlein在《最愚笨的一代》指出,美國大學生整體素質下降,語言能力減弱,專注力喪失和知識貧乏,「卻以爲一機在手,萬事皆曉,自信心爆棚」。
著名作家Susan Jacoby在《美國的無理性時代》一書中,指出當今美國的反智主義是史無前例的嚴重,體現在對於無知的「毫無羞恥感」,並漠視理性和客觀真理,而網絡就是背後的強大黑手。
無獨有偶,2021年內地官媒《新華每日電訊》發表了評論文章,稱「文字失語」(失去自如地用文字表達想法的能力)已成為嚴重社會問題。在問卷調查中,近八成受訪者覺得自己的語言愈趨貧乏,評論直指這是「重視頻/畫面,輕文字」所帶來「停思、無思、文字斷片」的惡果。文章呼籲戒除對網語和表情包的依賴,多用完整文字表達。
我們的香港又是如何的呢?古兆申先生有以下觀察:
「香港是世界上最不喜歡讀書的城市之一……熱衷上網的人,都是圖個方便,沒有時間去全面瀏覽,更無意去識別和認證真偽。他們只挑最簡短的看,甚至只看大標題和圖片。這種『方便法門』已成為大多數人獲得資訊、了解事實、進行判斷、決定立場和行動的唯一辦法及習慣……」
「在這場運動中,許多人看到的都是網上亂發的資訊,然後挑選符合自己立場的口號或宣傳圖片,深信不疑。而且還熱心地不斷轉發,以擴大其影響力。於是大部分討論都失去了實事求是的理性,爭議都變成了感情用事的立場表達。」
他的預測是:「雨傘運動中青年人的偏狹、狂妄、非理性和破壞法紀,預示了類似的災難。本港青年如果不了解自己的問題所在,他們能爭取到的,只能是民主遊戲下災難性的後果。」
文章最後,他有如斯建議:
「手機世代多半會想,Google一下答案就出來了,又何必花時間去讀書呢?但資訊並不等於學問、思想和智慧。後者包涵了道德、理念和哲學,以及對個體生命和人類整體有益的重要價值。這些元素,可以塑造我們的人格和精神,加深我們觀察及思考事物的廣度和深度。如果我們缺乏這樣的基本功,我們就無從分辨互聯網信息的好壞真偽,更枉論對社會、政治現實的正確觀察。」

執筆至此,我不禁想起了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的文學大家王鼎鈞的一段沉痛話語:
「大時代的青年是資本,是工具。我們振翅時,空中多少羅網;我們奔馳時,路標上多少錯字;我們睡眠時,棉絮裏多少蒺藜;我們受表揚時,玫瑰裏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時,早有人為你準備好墓誌銘。天曉得,因為熱血,多麼狹隘的視界,多麼簡單的思考,多了麼僵硬的性情,多麼殘酷的判斷,多麼大的反挫,多麼苦的果報。」(《關山奪路》,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