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末重臣 罹患痼疾
譚寶碩先生之文章《一點之心》提及曾國藩出生時身有蛇皮紋,被相士批為不祥之兆,一生多災多難,但其百折不撓,發奮圖強,終成大業,故事頗爲勵志。
關於曾國藩的蛇皮紋,曾為其幕僚八年的清代著名外交家薛福成在《庸盦筆記》有如此記錄:「曾祖競希封翁,……忽夢有神虯蜿蜒自空而下,憩於中庭,首屬於梁,尾蟠於柱,鱗甲森然,黃色燦爛,不敢偪視,驚怖而寤,則家人來報添曾孫矣。封翁喜召公父竹亭封翁,告以所夢,且曰:『是子必大吾門,當善視之。』」
這可能是曾國藩成名後的附會。讖緯之術或穿鑿附會,古已有之。薛福成更有以下回憶:「饒州知府張澧翰,善相人,相公為龍之癩者,謂其端坐注視,張爪刮須,似癩龍也。」成名之人,身上頑疾惡瘡也能被如此美化,前後相士的説法大相徑庭,令人莞爾。
但是,曾國藩的個案頗爲特別,因爲其中半真半假,假的是神話傳説,真的是其身上確有「蛇皮」(或龍鱗),而此「蛇皮」纏繞了他一生,這就是纏綿難愈的皮膚病——銀屑病(Psoriasis),俗稱牛皮癬。
銀屑病是一種免疫系統疾病,目前具體原理仍然未知。一般相信,主要是體內其中一種稱為「T細胞」的淋巴細胞受到刺激,釋放大量的腫瘤壞死因子,導致表皮的角化細胞新陳代謝速度過快,從而加劇角質層的角質細胞過度剝落,破壞了表皮的完整性。
皮膚在缺乏這層物理性屏障的保護下,會誘發掻癢感,繼而產生傷口,患處出現紅、腫、熱這些炎症反應,形成一塊塊增厚、銀白、鱗狀的碎屑、斑塊。至於爲何淋巴細胞受到刺激,則源頭眾多,除了先天家族遺傳外,與情緒壓力或免疫功能不佳有密切相關。
二、美法名人 同病相憐
說起患有銀屑病的名人,筆者馬上想到十八世紀末的法國革命家馬拉(La Mort de Marat)。著名的油畫《馬拉之死》生動的「創作」了馬拉被刺殺時的情景。此幅政治宣傳畫由法國畫家大衛 (Jacques-Louis David)一手策劃,渲染了革命的單純與神聖,遮蓋了馬拉的殘忍與狂熱。
《馬拉之死》構圖明快單純、莊重,運用暗淡沉鬱的畫面營造馬拉的「聖徒」形象。歷史學家對馬拉的描述是「個子矮小、形體畸形、面容醜陋」,但畫中的馬拉猶如一座希臘大理石美男子像,樣子很像文藝復興大師米開朗基羅的一件雕塑《哀悼基督》,具有一種高貴的美,猶如一位殉道者。畫家有意將馬拉的死表現得如同基督教的聖人一樣,他的犧牲是為了善,是為了普通人的福利。
但現實中的馬拉卻是一位革命恐怖主義的倡導者,實行專制獨裁統治,對於一切反對他的人展開了瘋狂的殺戮,極力鼓吹革命流血,肆意殘殺貴族以及一切他認為可以殺戮的人。在馬拉等人的主導下,沒有經過任何審判、因為莫須有的罪名,將近5萬人送上斷頭台,近40萬人受到水淹、火燒、集體炮轟等極刑而喪命。
馬拉爲何要泡在浴缸裏呢?這是因爲他患了皮膚病(很可能是濕疹或銀屑病)。巨大的情緒壓力與對革命的狂熱,以及時刻防止政敵的暗殺,使他的皮膚病加速惡化,皮膚瘙癢難忍,還起水皰,唯一能夠使他緩解的是泡在摻有藥水的浴盆裏,緩解皮膚皺裂之痛。

頑疾困擾 名人難免
問題是,如此浸泡在浴缸裏,對病情是否有效?現實中許多皮膚病患者會利用熱水的刺激,期望來抵銷劇烈的掻癢感。但是現實中,洗澡水溫過高會破壞皮膚表面的油脂,導致毛細血管擴張,加劇皮膚乾燥,導致病情進一步加重。此外,洗澡過勤,也會把皮膚表面分泌的油脂及正常寄生在皮膚表面的保護性菌群洗掉,容易傷害到皮膚的角質層,由此導致皮膚更瘙癢,皮膚的抵抗力也會減弱,形成惡性循環。故此,洗澡方式該以淋浴為宜,且不能有搓擦、搔抓,以免導致皮損部位皮損,引起感染。
馬拉如此長期浸泡在熱水中,療效確實成疑。而且,他一邊浸浴之際,也繼續工作,主要的「使命」就是記下他可疑的「反革命分子」名單,然後不加審訊就將他們送上斷頭台。在如此頑疾的困擾下,馬拉的情緒和判斷很難不受其影響,因而枉死在馬拉筆下的亡魂不知凡幾。
另外一位久受銀屑病困擾的是二戰時的美國海軍五星上將小威廉 · 弗雷德里克 · 海爾賽(William Frederick Halsey, Jr.)。2019上映的戰爭大片《決戰中途島》中由Dennis William Quaid飾演的就是這位人物。電影中這位剛毅決斷、性格急躁的美國第三艦隊司令,備受銀屑病所困擾,不停瘙癢,情緒極受影響。後來更因銀屑病惡化,影響了個人情緒與判斷,因此被上司撤換,不能參加中途島戰役。
如此安排甚爲合理,因爲銀屑病發作之時,令人產生劇烈痕癢、灼痛等不適感覺。患者指甲會出現凹陷、粗糙、坑紋的情況,更有機會令指甲變形或增厚,導致甲床剝離,嚴重患者甚至連拿取東西都會變得困難。更嚴重的就是從而導致的銀屑病型關節炎。而且,雖然銀屑病並不具傳染性,惟大眾對其認知不足,令患者飽受歧視,需承受極大的社交和精神壓力,甚至會產生自毀傾向。
三、日記中字字血淚
曾國藩的病徵與以上描述頗爲吻合。北大教授張劍在其2020年的新著《晚清高官的日常煩惱》一書中,首次披露了曾國藩日記中有關銀屑病發病的記錄。咸豐十一年,曾國藩的癬瘡大發,全身奇癢無比,爬搔至皮膚糜爛,其日記有以下記載:「瘡癢異常,意趣蕭索」、「遍身瘡癢,寂然寡歡」、「余以遍體瘡癢,兩手作疼,不能做一事,終日愁悶而已」、「余遍身瘡癢,坐臥不安」、「余向來怕熱,近年尤甚,今年遍身生瘡癬熱毒,本日酷熱,幾若無以存活者」、「遍身痛癢,幾無完膚」、「手不停爬,兩手兩臂皆爛而痛」、「癬癢異常,手不停爬,左腿已爬搔糜爛,皮熱作疼……近日,瘡徵痊而癬又作,悉身無完膚,意緒凋疏」。薛福成亦有以下回憶:「公終身患癬,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邀余圍棋。公目注楸枰,而兩手自搔其膚不少息,頃之,案上肌屑每為之滿。」
由此看來,曾國藩深受銀屑病所困,情緒極受困擾,實在是苦不堪言,痛不欲生。而由於其以漢人身份於清朝位極人臣,且面對滿清晚期最大的變局,所受壓力難以想像。在曾國藩日記和信件中,時而出現「生悶氣」的內容。例如 「余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駡;癸醜甲寅,為長沙所唾駡;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駡」、「慪氣從不說出,一味忍耐」。咸豐七年(1857年)他給弟弟的信就提到:「余在外數年,吃虧受氣實亦不少,他無所慚,獨慚對江西紳士。」同治五年,寫信給弟弟壯膽,提出他的處世名言:「打掉牙齒和血吞。」
如前所述,銀屑病會因爲情緒壓力而加重,曾國藩如此心境,對疾病更爲不利。曾國藩素來抗拒服藥,後來免於其難才勉強服藥,但觀其日記,藥方無效。直至同治元年(即1862年,距離曾國藩去世前十年),他的銀屑病忽然不藥而愈。日記中有如此記載「近日瘡癬少愈,不甚痛癢,不知何故。」
四、疾病與藝術創作
在疾病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如果相信人死如燈滅,死亡則是兩腳一伸,一了百了。但是疾病卻可以纏綿不愈,糾纏一生。究竟疾病與個人成就關係如何,難以一概而論。在藝術創作之領域,疾病似乎具有積極作用,特別明顯的就是精神病,西方有梵高、伍爾芙、舒曼、海明威等,東方則有徐渭、石魯、沙耆等。
如果根據法國哲學家傅柯的觀點,所謂的精神病只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建構自身、排斥異己的產物,並非古以有之。理性與非理性本是平行發展,而不是對立衝突。由此看來,所謂的精神疾病與藝術成就似乎有正向關係。
除了精神病外,對於第一流的藝術家來説,疾病似乎可以成爲創作的出口和動力。例如晚年患有嚴重眼疾、無法分辨色調的莫奈、患有類風濕性關節炎的雷諾瓦、患有嚴重腸道疾病的馬蒂斯、感染西班牙流感的愛德華 · 蒙克,還有患有梅毒的貝多芬等等。這些頂級藝術家,他們即使身患頑疾,卻以藝術對抗苦痛,甚至在疾病中形成更加敏感的觸覺和創作靈感,激發他們的天賦,就如蒙克所說:「當我染上流感時,我注意到一個人可以多麼極不情願地變得全神貫注,而且隨之而來將有更好的藝術品出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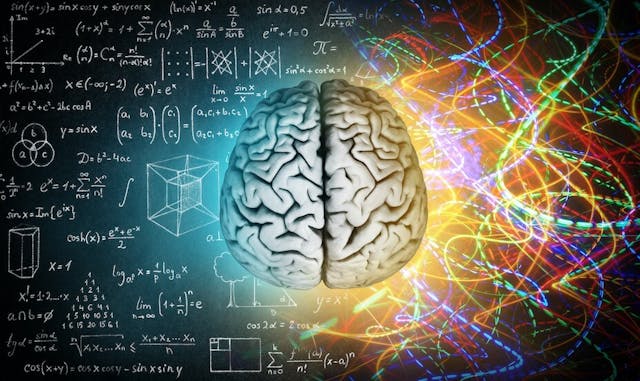
除此之外,文人羅患疾病的也不在少數,例如杜甫、白居易、蘇軾、劉禹錫和韓愈等有大量有關疾病的詩作存世。此外,民國時期疾病更被當作一種隱喻運用於文人的創作中,用來暗示此時國家和社會的狀態,例如魯迅的《藥》。另外,該時期不少文人都患有肺結核,像瞿秋白、郁達夫、冰心、廬隱等等,他們都將自己患肺結核的感知和經歷融入到自己的創作中。
在文化創作領域,固然可以無病呻吟,也可以藉病發揮,但除此之外,疾病帶給人們的該多是負擔和痛苦。例如在學術界中,患病往往意味着精力的減退,研究之路難以持久。歷史學家嚴耕望在《治史三書》中認爲做學術首要的是強健身體和健康心理。他舉出歷史大家陳寅恪為例:「我們這個時代的史學家群推陳寅恪先生為巨擘,以他天分之高,學養之深,語文工具之博備,誠為曠世難得之人才。」但陳寅恪一生未盡其才學,「我想陳寅恪先生大志不遂,最基本的原因是身體太差,又是悲觀主義者,自不勝負荷其志願。」
五、皮膚病與政治人物
這個規律和道理放諸波詭雲湧、日理萬機的軍政界更是合理,政界人士如想退下政壇,疾病和照顧家庭往往是一個相當體面的理由。這方面,香港讀者該有同感,並不陌生。曾國藩在如此頑疾之下,似乎並沒有影響他的運籌帷幄和政治才能,依然能夠成就一代能臣,該屬異數。
初步解釋有二:其一,是其具有驚人的意志力,以及秉持儒家忠君報國的信仰;其二,銀屑病最大影響就是外觀問題,以及帶來的情緒困擾,對心理健康影響嚴重,但身體功能卻無太多影響。即是一個身體健康,但情緒偏差(或抑鬱或狂躁)的狀態。曾國藩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倒是一個值得探討和學習的方向。
歷史上患有同類疾病的,包括中國的隋煬帝、開國元帥林彪、蘇聯的史達林、美國政治家、科學家本傑明 · 富蘭克林等等。根據網上資料,史達林曾重賞其私人保健醫生Kazako大夫,以表彰其治癒了他的銀屑病。但當史達林銀屑病復發時,其「御醫」卻束手無策,於是在1938年,Kazako大夫以「陰謀叛國罪」被判死刑。
下筆至此,筆者不禁想起了英國作家梅森(Phil Mason)2013年的著作《拿破崙的痔瘡》,他認爲拿破崙在滑鐵盧戰役中打敗仗,並非戰略出錯,而是因長期穿著緊身褲,導致痔瘡發作及惡化,影響了他的判斷力和意志力,歷史從而改寫。
以上並非新論,早於2000年出版的醫療史巨著《疾病改變歷史》對此已有分析。筆者突發奇想,如果將來如有《史達林的銀屑病》一書面世,也許可以從另一角度來詮釋蘇聯的近代史,以及用來解釋史達林的殘忍和嗜殺。
目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依然肆虐全球,不但改變了個人生活方式,也予世界格局重大衝擊,有見及此,疾病與人類的關係更值得我們深思。與斯賓格勒、湯因比齊名的現代歷史學家威廉 ·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獨具慧眼,自70年代已經把歷史學與病理學結合起來,從疾病角度來重新解釋人類行為,成就斐然。
常人患病,徒嘆奈何,影響有限,但手握大權的大人物則牽一「病」而動全身,影響深遠。銀屑病如何影響這些歷史上大人物的性格、思路、行爲以及決策,確實予人無窮的想像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