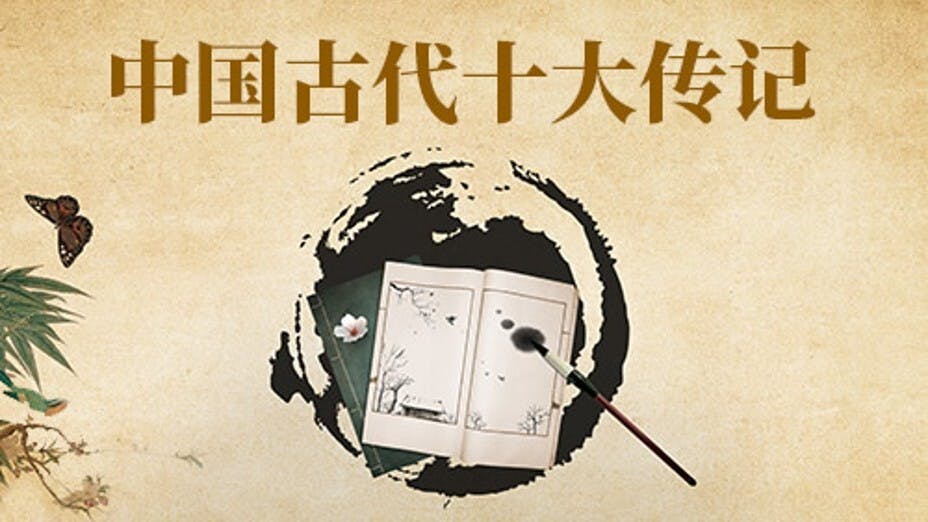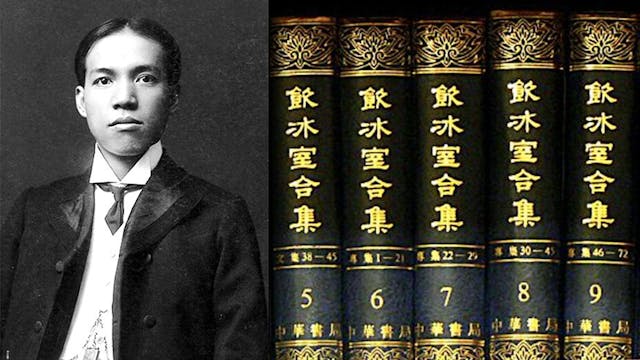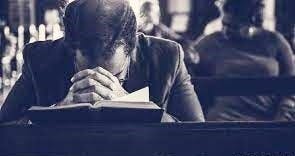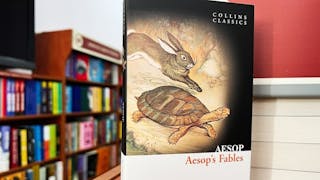承接前文:〈接近天堂的地方──巴黎掃墓隨想〉
相比起西方,中國的墓誌銘就繁複得多,內容分為誌文和銘文,前者記事,後者頌贊,全文統一,講求工整,多為蓋棺定論式的評價,蘊含道德規範。而有關墓誌銘的源流,基本上認爲是起源於東漢,普及於魏晉六朝,真正的繁榮期則在唐代。

中國墓誌銘的三大特徵
第一是避諱死亡。儒家思鄉以現世的積極,壓抑、避開了死亡意識,故此,中國墓誌銘中,多用其他詞語代替死亡,例如歿、故、卒、逝、殤、作古、殞、薨、崩、仙逝等予以避諱。此外,也用上華麗莊嚴的辭藻來作為修飾,例如「辭光白日,掩駕松山」、「淵珠墜壑,玉碎荊山,大夜一深,白日不旋」等,如此也表達了對死者的哀思。
第二是以「死者為尊」。不論死者生前如何,過世後則極盡頌揚和追思,例如《皇甫驎墓誌》稱讚其才情「三才啟曜,五氣流暉。名川峻阜, 靈感特微。……綽矣高度,希世間出」;《楊穎墓誌》稱讚墓主楊穎「君資性沖邈,志秀天雲, 情高古列,不橈下俗」。如此導致「諛墓」之風盛行,存在過於溢美、浮誇不實的現象,影響相當深遠。
第三就是傳記與記事的特徵。這種寫法具有重要的史學、文學和藝術價值,就如榮新江指出:「墓誌提供的細節之豐富是驚人的……墓誌也是古人用來表達其自我認知的重要空間。」故此,墓誌銘能夠起到證史補史的作用,是研究古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生動的「參考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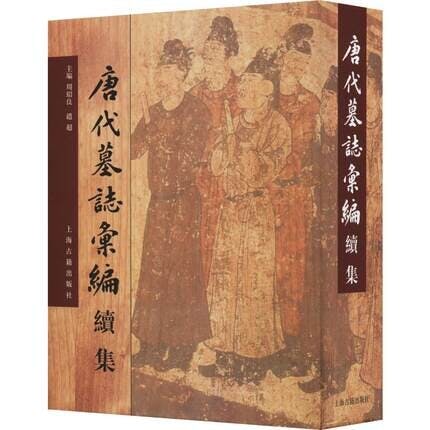
「諛墓」之風與「名人」傳記
「諛墓」即墓誌銘上那些過於溢美、浮誇不實的普遍内容。如此風氣,也同樣反映出中國傳統傳記中,存在着「曲筆詢情、無美稱美、弄虛作假、微功過褒、誇大失實」的諸般弊端。
有見於此,偶有文人對之提出批評。例如南朝的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設立了《誄碑》篇,提出了墓誌銘寫作要「資乎史才」,才能「必見清風之華」,達到「其序則傳」及「其文則銘」的效果;而宋代文學家曾鞏亦在《寄歐陽舍人書》中批判了「諛墓」之風,認爲「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

他認爲只有品德和文采具高的人,才能勝任撰寫銘文的工作,而評論公正和文采斐然的墓誌銘,可以使善人「勇於自立」,使惡人「以愧而懼」,達到教育和感化的「警勸」功用;歐陽修的看法更是精到,認爲撰寫墓誌銘必需文簡而意深,含蓄蘊藉,實事求是,切勿虛美妄言。
當然,這類聲音在傳統社會屬於極少數,現實中也難以執行。例如曾鞏雖不屑那些「褒揚其親」而失實的墓誌銘,但自己也無法免俗,犯了同樣錯誤。他請歐陽修為祖父作墓誌銘時,提供了一些有關自己家世的材料。歐陽修認真閱讀後,發覺他所敘述的先世事蹟多屬虛妄,考之《史記》皆不合。故此歐陽修專門寫了《與曾鞏論氏族書戶》,批評曾鞏「於氏族尤不明其遷徙,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
如此風氣,也難怪民國時期的胡適發出如此批評:
「傳記最重要的條件是紀實傳真,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卻最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不失於諛頌,便失於詆誣,同為忌諱,同是不能紀實傳信」;
「中國的傳記文學,因為有了忌諱,就有許多話不敢說,許多材料不敢用、不敢赤裸裸的寫一個人、寫一個偉大人物、寫一個值得做傳記的人物。」
梁啟超也持類似觀點,認為中國古代傳記:
「幾乎變成專門表彰一個人的工具。許多人以為中國史的最大的缺點就在此處。這句話我們可以相當的承認。因為偏於個人的歷史,精神多注重彰善懲惡,差不多變為修身教科書,失了歷史性質了。」
傳統基因下的中國式傳記
可以說,傳記家能否寫出真實,相當受制於時代的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中國的情況很複雜,儒家的人性論與政治上的意識形態對傳記形式影響很大。
儒家標榜「性善論」,既然人性本善,那麽即使犯下過錯,也是可以改正的。這可以是寬容,也可以是寬鬆,更可以是缺乏約束的縱容;而政治上,三綱五常和政權穩定是主要的意識形態,重視道德規範和示範,如此情況下,就出現了史學家劉知幾所說的:「惟聞以直筆見誅,不聞以曲詞獲罪」。
故此,中國式的自傳,較容易流於自我美化或辯解,文筆中難免隱瞞和忌諱,以及高度的選擇性。如此情況下,自傳的最大功能很可能淪爲自我宣傳和自我辯護,難怪日本漢學家川合康三認為:「中國文人寫自傳,歸根究柢都是為了強調自己的正確。」
這裏也包括在美化和辯護中,輕易地原諒自己的過錯。魯迅在《論睜了眼看》一文中,狠辣地批評了這種現象:「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

如此文化基因,影響深遠,譬如對真相和真理的視若無睹,毫不在乎。我們的社會之所以出現名人式的「亂噏當秘笈」,信口開河,毫無顧忌,受眾也司空見慣,麻木無感,還是與我們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有關港式名人的胡言亂語,可參考拙文〈論土豪式亂噏〉)
神學注視下的西方傳記
西方的情況就很不一樣。可以說基督教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西方傳記的本質。按照基督教的「原罪論」,人不但有與生俱來的「原罪」,而且在現世生活中還會繼續犯下各種各樣的罪行。故此,在上帝的面前人人平等,都是罪人,「罪感文化」已成為西方人的普遍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既然人皆有罪,那麽人的一生就是「救贖」,是在上帝的指引和感召下棄惡向善的過程。故此傳記在原則上並不回避主角的缺點、弱點和犯下的罪過,自身有罪的人也無須掩飾。《舊約》的傳記作品中就記錄了那些希伯來偉大君王所犯下的罪過,可以說,西方的自傳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反映出一種坦白和懺悔的精神。
《聖經》是了解西方文化的起點,也是終點;要理解西方傳記文化,也必須從《聖經》入手。研究者發現《新約》中的〈保羅書信〉最具自傳色彩,也對西方自傳敘事產生了最大的影響。他的書信對於我們理解西方式的自我觀念、自傳衝動及深層動機都頗有啟發。
而英國學者彼得·阿博斯(Peter Abbs)對於《舊約》與傳記的關係有深刻洞見,說出了西方宗教下的大眾心理模式:
「與大部分古典作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舊約》常常表達一種激烈的個人渴望,這種渴望拒不接受任何世俗的調解和安慰。比如《約伯書》和《詩篇》就表達了一種焦躁不安、源於靈魂內部的追求以及一種對於整全和拯救( wholeness and salvation)的熱切渴望……在《新約》中,人對於生與死問題的急迫感下,賦予了以下問題以特殊的重要性:直接見證、直言不諱、外部行動的內部動機,以及分享希望與狂喜的經驗,這些都是在後世的自傳中發展出來的傳統。」
這些都是相當值得深入研究的好課題,有助透過參照他者和了解自身,來反思自我。如此學術風氣,也折射出「罪感文化」中的反省意識,依然比所謂的「樂感文化」強烈得多,也清醒得多。
寫到此處,我不由地想起臺灣散文大家王鼎鈞的《回憶錄四部曲》。這位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的散文大家,在個人回憶和客觀事實之間,拿捏得相當到位,冷靜得無以復加,這需要清醒的歷史意識和文學自覺,也與他的基督教信仰息息相關。去年因雷先生之故,我與此書結緣,拜讀之下,擊節讚賞,其文字千錘百煉,態度冷靜從容,令人心折。
在此,也將王鼎鈞先生撰寫回憶錄的一些心路歷程和感悟,稍作整理,予有緣者一起分享。
巴黎掃墓隨想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