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可以治國,科學可以強國。沒有經濟,如何富國?沒有教育,如何興國?

貞觀二年春,玄奘在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的官員陪同下,離開素葉水城,輾轉到達颯秣建。但玄奘反而迂迴地多走2,000餘里,進入Fergana盤地繞了一個大圈,原因耐人尋味。

在經歷過不少的複雜的人情世故之後,提煉出來的是處世智慧是認命:你最「叻」了,我最蠢了,有什麼好爭呢?

30年來多次到新疆,只因為對新疆有一種痴迷。逐漸認識新疆,見證許多變化。

玄奘離開高昌國,沿着西域諸國越過帕米爾高原,在異常險惡困苦的條件下,終於到達天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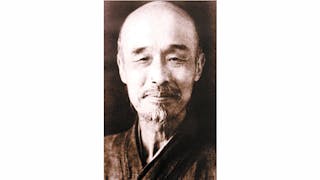
弘一法師在63歲臨圓寂之前,寫下令人感懷的「悲欣交集」四個字。這幾個字可以看出他對死亡離世的態度。

中國學者若要認真地進行對絲綢之路國家的探索,就應該從一帶一路的具體建設中獲取啟發與資料,開闢新課題和做出新論述。

聖母神學院默默地守在大嶼山東岸近60年,一直鮮為人知。院內的隱修生活及中世紀傳統,都是香港罕見。

持東方主義態度的人,被認為是抱着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帝國主義態度來理解東方世界,又或對東方文化及人文的舊式及帶有偏見的理解。

在毛澤東看來,若是缺少了中國文革那樣的革命運動,即便俄國有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也是保不住的,廢於半途,一整套正宗社會主義制度都變色變質、徹底潰爛。

《聖經》記載,逾越節將到,當耶穌騎着驢駒抵達耶路撒冷城時,許多人把衣服脫下鋪在路上,有些人把田間的棕樹枝砍下拿在手中搖動,歡迎耶穌一行人進城。

水務署大量的署內署外活動,消除了分部、職系和級別的隔膜,活動中的合作則加強了公事上的合作。

黃淑琪的《可以居》,給西貢白沙澳注回活力,是本地一個上佳的藝術嘗試,拓闊了創作的領域,於媒體交結中想像生活的多樣可能,並展示了新穎的藝術可居的方式。

漆俠先生學術道路深受20世紀中國實證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是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漆俠先生治史領域寬廣,側重中國農民戰爭史、中國古代經濟史和宋史,在這些領域均取得很高成就。

一些來自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島國的學生,最關切的問題不在於中國文革的國內層面,而是它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和更大範圍內國際政治的影響。

員工若對崗位或工作環境不滿,難有出色表現。2000年代中期,水務署訂立了詳盡的監工輪轉調職機制,在運作效率和擴闊員工經驗取得平衡,工會發出會員通告,大讚署方安排,這種情況在政府部門相信甚為罕有。

早於1960年,位於荷李活道的《華僑日報》報館,曾被多齣電影借用作外景場地,包括《蘇絲黄的世界》、《胭脂扣》等。現今原址已拆卸重建,令人感觸。

蘇軾一則「未嘗輕以示人」,寫給友人也要千叮萬囑,期望「深藏不出」。很顯然他是怕由此而惹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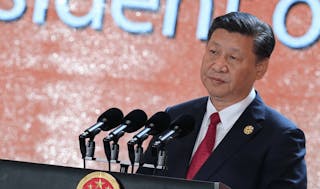
中國目前具有強勁的經濟動力,豐沛的金融資源和雄厚的科技實力。這些優勢對新絲綢之路的建設,都十分重要。

蒙古帝國衰落後,歐亞大陸上陸權至上時代告一段落,海權逐漸取代了陸權,成為歐洲國家日後稱霸世界的基本條件。

梁偉傑老師認為中學生讀歷史書的心態是被課程框架牽引着,只講求簡單易讀和為了考公開試,沒有真正享受研讀歷史的樂趣。

今年正值蘇曼殊逝世百年紀念,他生於中國動盪的年代,給我們留下傳奇的生命痕跡。

北京方面事前收到情報,知道有人會對中國代表團搞破壞,已循外交途徑通知港英政府留意飛機在香港停留加油時的安全,但仍百密一疏。

譚家齊博士認為面對互聯網和大數據等新環境,再加上人工智能對未來教學的介入。新生代的史學家不能繼續抱殘守缺,必須要學習傳統史學以外的數理應用知識。

尖沙咀海員之家會所已有50年歷史,設施陳舊老化,遠低於現代化標準。地產發展商規劃建一幢樓高33層高的綜合性酒店及會所,設施功能將根據社會進步,環境之下新需求,或會有適當調整。

新中國成立後,香港的英國人也明白到需要改變,於是有貝納祺(Brook Bernacchi)的「香港革新會」的出現。

蒲苔島位於香港最南端,島上遍布奇岩怪石。蒲苔島有兩大熱鬧節日,天后誕和太平清醮。相對於新界大型鄉村的太平清醮,蒲苔島的打醮規模較小,前來恭賀的外面人士不多,反而專程由香港仔到來觀戲的人不少。

作者深感如果不想學生在文革課堂裏鬧場,就不應強迫學生接受任何論點是唯一的正確觀點,即使教師堅信某個論點也要盡可能拓展學生視野和深化他們的比較研究觀念。

當今「手機快拍」氾濫,可曾想起在彩色攝影未普及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其實大部分的彩色香港影像,都是來自外地遊客在港遊歷時的快拍?他們用上35米厘膠卷相機,在不經意按下快門的一刻,已為歷史留下珍貴的定格。

1918年2月26日,跑馬地馬場發生了一場致命大火,造成670人死亡。適逢早前是大火100周年,重溫這次慘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