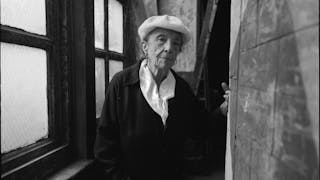新奇?像新奇士橙,我都吃過了!還有其他新絲蘿蔔皮?
藝術,像不安於座的小朋友,走來走去,尋求突破,搞搞新意思,但受眾者宜冷靜,觀察那些藝術新浪潮,能否真的可以站穩住腳?因為藝術的正統和非正統界線正在消失,同樣地,high-art和low-art也變得朦朧不清……
最近幾年流行沉浸式劇場(immersive theatre),它改變傳統的形式,即演員在舞台上表演,觀眾坐在下面座位欣賞,突破劇場以往空間的限制,改變了觀眾只是安坐座位的做法。這些表演常加以影像投放、立體音響等電腦新科技,讓觀眾既有新鮮感,又可參與表演,重新把表演者跟觀眾的角色整合,打破觀眾和演員之間的fourth wall(第四道牆)!
老前輩說:「太陽之下無新事!60年代,香港街頭表演,又唱又跳,然後邀請圍觀者玩埋一份,那不是immersive theatre嗎?」我點頭:「在灣仔春園街,我看過路邊的『鳳陽花鼓』表演,藝人拉小朋友打花鼓!」前輩點頭:「記得當年九龍城寨的脫衣舞,舞娘叫叔叔們一起脫,也是沉浸式!」我笑:「那是『淫』浸式!」
難忘體驗
這十多年來,在香港和外地體驗過不少immersive theatre的演出,只恨沒有看過著名的《無眠夜》(Sleep No More):大型製作,目不暇給,觀眾和演員們一起「玩」,讓大家走入莎士比亞小說的世界。
在香港,我難忘兩次沉浸劇場的體驗:當年去了黃竹坑的工業大廈,那次的主題是「軍訓」,入場觀眾要忘記現實身份,假想自己是剛入伍的士兵,然後被長官指揮工作,如操練、煮飯、偷襲敵方……但是,被他「點到頭都暈」,我是老人家,玩了一小時,精盡人亡,偷偷溜回家睡覺。另一次去葵青劇院,觀眾要走上舞台,台上劃分四個場景,有四個不同表演:粵曲、話劇、音樂等。我們分批圍着表演者,望、聞、問、切,短時間內要分心看幾個演出,只感到累透。
沉浸劇場,主要分五類:第一類,是簡單地觀眾和演員互動,例如觀眾扮陪審團,演員扮法官,一起審理案件。在日本,時興數十位觀眾圍着一個演員,合做對手戲。第二類則把場景搬去戶外,例如是鬼屋,觀眾和演員一起歷險、捉鬼,而戶外場景可包括教堂、醫院等等。第三類是密室逃脫,我在九州玩過一間瘋人院,裝瘋的演員隨機襲擊觀眾,大家急忙逃生。
此外,最普遍的叫ASMR(autonomous sensory meridian response),例如日本的teamLab公司的作品便接近:藝術家、程式設計師、工程師、CG動畫師,在數千呎的密封地方,蓋搭不同主題的場景,如森林、天空、科幻世界,觀眾通過四周裝置的感測器(sensors)和場景互動。我玩過一個以名畫家梵高為題的ASMR,場景內,投射他的畫作,然後觀眾可以和梵高的幻象對話,那絕對是戲劇、科技和美學的融合。
第五類常見的叫GSI(grand spectacle installations,大型壯觀裝置),例如內地大型節目的開幕shows,景象不停變換,悅目娛心,我在外地看過一次雷電交加的奇技淫巧,幾可亂真。當GSI運用在室內劇場,技術可包括3D立體影像、座位震動、香味噴射、灑水向臉,有時候,觀眾更要戴上VR眼鏡,加強三維空間虛擬世界的效果。這些表演的存在價值,常在於它的娛藝創新性,我不大感受到戲劇藝術性,只像去了環球影城看魔法世界。
跟表演者保持適當距離
沉浸劇目在外國,已發展到機械人在特技配合下單獨表演,但那些表演完全沒有人氣,有啥好看?所謂immersive theatre,今天已去到超賣現象!
作為觀眾,我喜歡被動,不喜歡和演員互動。看表演是為了視覺、聽覺和心靈的享受,而不是去做運動,郁手郁腳、走來走去。也許阿叔我已臻化境,這些玩意感動不了我。在潮流文化中,「新屎坑」往往「三日香」。
和表演者保持適當距離,我覺得是對他們的專業尊重,要求演員四處行走、和觀眾談笑風生,其至和觀眾一起品茗猜詩、狂歌熱舞,有點過分。此外,觀眾又可以隨意翻看道具,甚至參與改編劇情,這些劇場除了模式新穎、吸引年輕人以外,我覺得完全不尊重表演藝術,因為演員和觀眾的莊閒難分,專業和非專業的界線也變得糢糊,給藝術「塗漿糊」。而且,下一步,再可以有什麼突破呢?聽說:內地沉浸式戲劇《知音號》把表演場地設置在一隻船上,唉!聽到都暈船浪!
當文化藝術界天天把「沉浸式」掛在嘴邊,不斷加持,那兒新鮮,便往那兒擱着去,藝術從業者真的要小心炒車。記得:妹仔不能大過主人婆,喧賓奪主。戲劇的真正成就,在於觸動觀眾的心靈,好的故事,好的演技,才是玉液瓊漿,其他只是supporting:當劇情不騷、演員不羶,味精煮不了一碗靚湯!
是我的想像力不夠,還是科技發展未去到讓我100%投入,每次看這些沉浸式表演,還是那一句「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不如,別耽誤時間,快回家玩電腦,精彩的Apple Vision Pro等着,更容易把我沉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