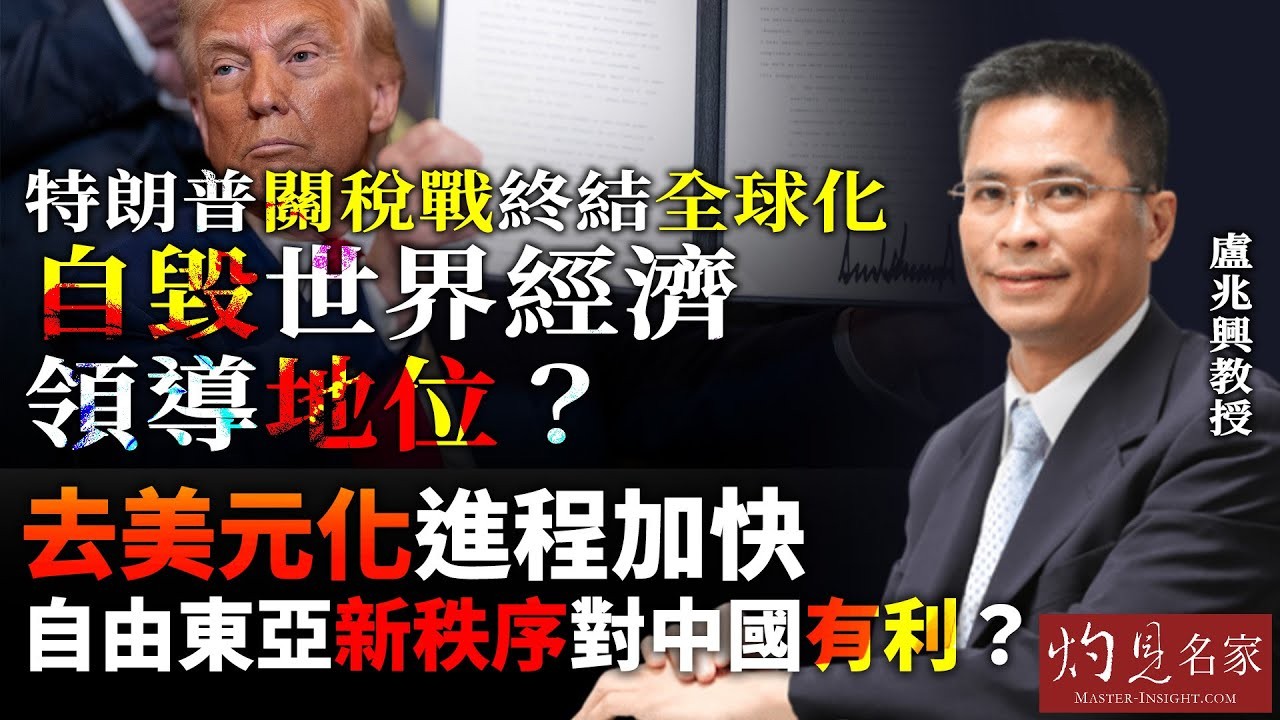上周五(2月28日)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內,美國總統特朗普、副總統萬斯跟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談期間,在一眾記者面前高聲互罵,雙方最終不歡而散的片段,可謂舉世矚目。此外,早前美國與俄羅斯就俄烏戰爭展開停戰談判,亦惹來了「第二個《慕尼黑協定》」的憂慮和猜測。就在坊間普遍等看特朗普的鬧劇與笑話,或期盼特朗普下一盤大棋的兩極之間,以一個體系性的角度來解讀特朗普之大戰略,或許更能夠一窺其全貌。
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目標,其最大化固然是取得一種冷戰式的勝利。但在特朗普僅4年的第二個任期內,要達到這目標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反而,阻止美國霸權衰落的趨勢、扭轉美國整體國力下降、解決龐大財赤和債務,以及面對中國崛起的挑戰,令美國霸權永續或不墜,卻是更迫切及更需正視的問題。而特朗普似乎有從上一個衰落的霸權英國的錯誤政策中汲取教訓,以避免美國衰落。
霸權衰落論:英國的例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儘管英國成為了世界歷史上面積最大、跨度最廣的國家,但只是在表面上維持着超級大國的架子。英國總體上仍是淨債權國,唯英國對美國的負債總額當時卻達到47億美元。這是國際金融權力由英國向大西洋彼岸轉移的徵兆,也預示着未來英國將會愈來愈多在各方面依賴美國的支持。另一方面,戰前支持帝國經濟繁榮的那些支柱產業──煤炭、鋼鐵、造船、紡織業──都面臨長期衰落的局面。整個1920年代,失業率居高不下,英國的貿易逆差愈來愈大。雖然在1920年代後期,國家仍有曇花一現的對經濟繁榮的信心和希望,但一切希望都在1929年開始的全球經濟危機面前灰飛煙滅。

很大程度而言,經濟與財政問題是使英國極為虛弱及步向衰落的主因。面對當前美國的財政黑洞、天文數字的債務負擔,對於這個美國霸權的最大破綻與隱憂,特朗普不會坐以待斃。馬斯克警告,每年2萬億美元的政府赤字令美國不能持續發展,將會破產。因此特朗普政府的減赤滅赤措施及關稅戰,必然會是「窮凶極惡」,連那些無法想像的手段都要考慮,並必須盡快行動。美國眾議院日前通過特朗普提出的預算決議案,未來10年減稅4.5萬億美元及減開支2萬億美元,這仍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顯示美國經濟正在走下坡,必須以減稅重振經濟。
從英國的例子也可看出,假如美國墨守成規地維持它所創立的國際秩序、建立國際合作安全機制、通過外交協商來解決國際爭端、不惜一切代價維持世界和平,最後很可能只會步英國的後塵,徒增霸主的自我損耗,一個不好,甚至連霸權也會一併失去。而之前拜登的外交政策,雖堪稱是自由國際秩序的典範,但其實質意義與一戰後英國的政策並無二致,最多只能多促成美國霸權軟着陸或推遲其衰落,卻不足以扭轉原本格局。

葬送霸權的元兇
英國經濟與軍事力量的衰弱,固然是其霸權衰落的最根本原因。唯真正葬送英國霸權的,卻是它一次又一次缺乏足夠能力執行的安全保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了確保比利時的中立而向德國宣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同樣是為了保證波蘭的獨立而向德國宣戰──在未具備充分條件下,因自己開出的「空頭支票」而被迫捲入戰爭。
由此可見,戰爭是失落霸權和權力轉移的最重要契機。因此避免被迫捲入戰爭,可說是使霸權不墜的一門重要學問與藝術。這次澤連斯基與特朗普的會談雖淪為鬧劇,但特朗普希望盡早尋求和平,並表示美國將不會繼續在戰事中無限支援烏克蘭,以及沒有立即或無條件向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無疑具有一定的戰略意義,有助將美國從準戰爭狀態中釋放出來,並非全無道理。

至於俄烏戰爭,亦進一步暴露出以北約為重心的二戰後同盟體系的無力與尷尬:一個佔全球國防開支70%以上的軍事同盟及陣營,一直只能夠對烏克蘭提供巨額的軍事援助,以及對俄國實施制裁和譴責,卻又不敢讓烏克蘭加入北約;為首的美國也拒絕把美軍部署在烏克蘭,導致戰爭淪為一場長期膠着、傷民勞財的消耗戰。現在美國雖未至於像以往英國般被盟友或安全保障拖入戰爭,唯俄烏戰爭明確顯示北約和歐洲國家必須改變,同時美國也有理由選擇踐行一個不以軍事同盟或同盟體系為核心的霸權模式。
新帝國時代的來臨
儘管特朗普經常胡來及語不驚人死不休,但美國確實也到了一個必須改變其一貫二戰後角色的時候。與此同時,二戰後或冷戰後的世界秩序亦面臨重大變遷。我們可能將迎來一個「後單極霸權時代」,即使有霸權存在,也不一定會帶來穩定,唯也不會一下子演變成一個多極世界。相對於以前由一無所有的國家(have-nots)挑戰現有霸主(haves),這次世界格局的改變,更可能由霸主或大國演化成的「帝國」所帶動。這裏不是說特朗普將登基為「皇帝」,而是霸主或大國的行徑將愈來越愈一個帝國。特朗普美國的行徑正反映着這一趨勢──它作為一個霸主(have),為了避免霸權衰落而採取一種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的行動,積極為國家謀取利益,從別國拿取好處,也不排除日後俄羅斯與中國也會發展出類似傾向。這或許反映着一種歷史發展的規律。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