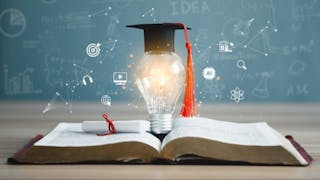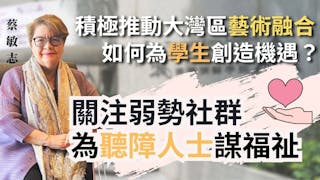新年伊始,也許是通過回顧而前瞻,通過環顧而反思的日子。在此闡述一下筆者個人的看法,與教育工作者、家長與社會其他朋友分享。
還是筆者那句老話:學習是人類的天性,教育卻不是。教育是人類為人類設計的學習系統。自然界的動物,也有天性的學習;他們的父母,也會引導他們的雛兒去學習適應生活;但那是順應各類動物的天性,父母引導他們去適應自然環境,盡早去過獨立的生活。但是其他動物沒有直立,沒有騰出來的雙手,沒有改造環境的勞動,沒有超越聲響的語言,也因此沒有愈來愈複雜的群體社會。
人類出生以後,就脫離了自然社會;他們需要的學習,就遠遠超過適應自然環境(例如步行);他們需要的學習,更重要是能夠在複雜的社會中生存(例如起碼是語言)。這就是我們的教育!

不過,人類社會是不斷變化的。因此在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階段,人類需要的適應也會很不一樣。參觀三星堆博物館,就自然想起,「當時的孩子需要學的是什麼?那時代,教育是什麼意思?」參觀科舉博物館,就不禁想問:「科舉是教育嗎?當時及第的是小眾,大眾的教育是如何發生的?」
所以,筆者上面那句話,連帶着一個觀察︰「因此,教育是人為的設計。教育總是帶着時代的烙印──經濟的、制度的、政治的、文化的、信仰的⋯⋯」這些話背後的潛台詞是:「教育是會過時的!」
時移世易,教育能不改變?
因此帶出一連串的觀察:一、即使當時影響的是小眾,科舉的「功名話語」,雖則純為選拔官員,卻塑成了中華文化的教育傳統。二、現代的學校教育體系,來自於工業社會勞動力的需要,是製造人力資源的「經濟話語」;形成與社會勞動力結構相仿的教育金字塔,影響全民。三、兩者同樣崇尚競爭、擇優、淘汰,因而跨代合流,形成了華人社會特別嚴峻的應試文化。四、社會又向前走了,逐漸走出工業社會嚴格、穩定、可測的科層結構,因此教育也需要改變。這些,可以說是本欄近年不斷重複的主題。此處不贅。
但是,教育如何才能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筆者雖然不斷在探索,但是還不算已經有了答案。這裏面試舉一些反面的觀點。

一、「教育就是這樣的」。持這種看法,並不一定是保守派;他們也不滿現狀,也希望變革。但是在這樣的思維裏面,覺得教育的框架大概就是如此,不是變革的目標。比如說,大批學生在一個大課室排排坐,一起聽教師講課,學生按年齡分年級,同年級的學生學同樣的東西,用基於有限的內容、簡單的考試來測評學生等等。雖然,其實每一樣都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歷史上,有不少西方學者詬病這樣的學校制度。最早也許是Ivan Illich的Deschooling Society(出名的《廢校論》,1971年),吸引了不少讀者,不過一般都覺得這是極端的理想主義。筆者曾經在巴黎聽過他的演說,老實說,長串長串的句子,不斷冒出的獨創名詞,實在聽不懂,但那畢竟是傳世的經典突破。隨後還有幾本當年頗為流行的書──Compulsory Miseducation、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The Diploma Disease、The Credential Society等等,都是深痛惡絕地詬病流行的學校制度。不過那是1970年代,反映批判性思維的社會覺醒。但也都沒有提出前瞻性的方案,那也許不是這些學者的職責。
後來,雖然各式各樣的教育研究遍地開花,但就執牛耳的美國來說,絕大多數教育研究都以學生成績作為教育的「產出」,下意識地鞏固了「經濟話語」的教育框架。

無以替代 所以保持現狀?
沒有前瞻性的替代方案,也許是「保持現狀」一個關鍵的原因。不是刻意要保持現狀,但是對現狀已經習以為常,「不這樣,又可以怎麼樣?」是通常遇到的反問。
最明顯的是關於競爭與篩選。但是許多人骨子裏會問:「不競爭,哪來動力?」家長會說:「不排名,我怎麼知道我家孩子表現如何?」(這裏的「表現」,是指競爭中的表現,不是學到了什麼;又回到了「功名話語」。)也會有人說:「總得有篩選吧!不然僱主如何甄選人才?」又回到了人力資源「經濟話語」:把學生的一生命運,寄託在僱主的一時需要。
二、覺得「教育裏面有些元素應該是恆久不變的」。這種看法,也是積極的──不要在形式和制度上花費精神,而應着力發揮教育的真諦。筆者認為,的確,教育有她核心的價值與功能,就是讓學生能夠在他們未來的一生中,有一個健康而有意義的生命。這裏不打算展開闡述這一點。想說的是:歷史上留傳下來的教育觀念與制度,並不能讓學生掌握未來、掌握生命。
延綿1300多年的科舉,在當時來說,正面看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不二法門。從王朝的維持統治,到個人的社會上升(魚躍龍門),盡在科舉及第。當年的讀書人,說不定也有不少「讀聖賢書」之中,果然有了「平天下」的宏願;也許有不少就只是朝着「書中自有黃金屋」而奮力。用今天人們的認識,難以判斷當時的是非利弊。但是,畢竟這是一種「功名掛帥」的機制──有了「功名」,才談得上其他。放在今天,也會有家長說:「別的先不說,讀好書,考好試,最重要。」也往往造成「只講分數,不論內涵」的效果,也造成了(已經不存在的、科舉的)「一試定終身」的假象。

培養技能 就是教育功能?
工業社會的「經濟話語」、競爭機制,把學生置於被動的、被塑造的地位。教育需要配合社會勞動力的需求,把人轉變為人力資源。這在十九世紀中葉,現代學校制度出現的年代,也許是符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樣,用今天的眼光,難以判斷當年的是非利弊。但是今天,社會的金字塔型科層結構正在退出歷史舞台,穩定的職業、行業結構,也正在逐漸趨於渙散。
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現在各國流行的學校制度只有不到200年歷史。說得嚴重些,正是這樣的學校制度,割斷了人類的教育歷史,讓教育負起純粹工具性的責任。直到現在,還有人不斷提倡美國在上世紀末提出的「二十一世紀技能」;筆者近日參加國際會議,充斥會場的是如何讓學生掌握人工智能;各國如有課程改革,都是如何加強科學教育、STEM。也就是說,正是現在根深柢固的學校制度,讓人們忘記了教育裏面恆久不變的要素。
那麼,這些要素是什麼?以下可以是一個小小的起點,供讀者參考。
還是那句話:從培養人的角度看培養人才,與從培養人才的角度看培養人,很不一樣。培養了堅強的人,就不愁沒有人才。這不等於就不要學習專門的知識與技能,但是學一門專門的技能,是為了學會學習,將來能應付不斷而來的學習需要。相反,若是學習專門技能就是為了對口就業,那仍然是工業社會製造人力資源的思路,遲早會遇到現實的挑戰。
更重要的是,有能力,並不就等於對社會有用。光有能力,完全可以成為社會敗類。培養了有健康品格的人,才會有對社會有用的人才。這要靠家庭的熏陶、學校的氛圍、師長的楷模、同儕的影響等。說起來彷彿有點抽象,但事實上我們環顧就可以看到,例如學校的氛圍,深刻地影響着學生的情緒和價值觀。在有些學校,學生整天沉浸在和諧、積極而從容的氣氛之中,學生產生抑鬱的可能性就大大減低。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