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日,移居美國多年的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李澤厚在科羅拉多州逝世,享年91歲。內地的社交媒體、網媒報道李澤厚去世的消息鋪天蓋地,知識界和文化圈也有不少人發文悼念。
易中天:李澤厚當年是何等了得
作家易中天在他的微博這樣寫:「剛剛得到李澤厚先生仙逝的消息,不禁愕然。20年前,我發表〈盤點李澤厚〉一文,對先生的學說有贊同有批判。先生不以為忤逆,只是當面對我講:『你可以說,我可以不聽。』又對我提出許多善意的建議。當時匆忙,未及深談,孰知竟成永別。悲痛之中,忽然領悟先生何以要用『子曰如之何』與『佛云不可說』為他的《世紀新夢》作結。謹以此意,敬獻輓聯致哀:
天或有情,佛云不可說;
人其無力,子曰如之何。」
20年前,易中天在〈盤點李澤厚〉一文寫道:「想當年,李澤厚是何等了得啊!80年代的大學生、研究生,有幾個不知道李澤厚的?就連他那本其實沒多少人讀得懂的《批判哲學的批判》,也是許多青年學子的架上之書、枕邊之物。……然而今天的大學生,已大多不知李澤厚為何許人也了。老話說,30年河東,40年河西。白雲蒼狗,本是當然。但,從80年代初到如今,不過20年光景,李澤厚就『過』了『氣』,無乃過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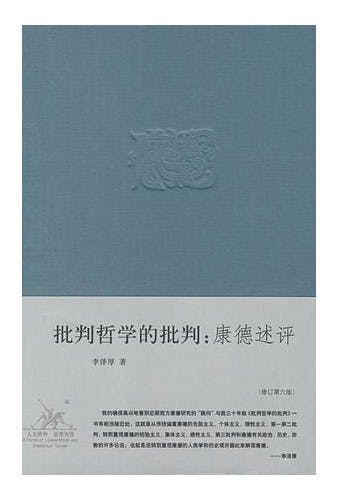
緬懷80年代風潮驟起
李澤厚20年前就「過氣」了嗎?筆者不知道。但是,他的著作《美的歷程》,在上世紀80年代的「美學熱」中,成為不少大學生的讀物倒是不假(當然還有朱光潛的《談美》)。他在《中國現代思想史論》中揭櫫五四運動的「啟蒙與救亡雙重變奏」,也風靡了不少讀書人,自然也招來大量批評。李澤厚的前同事、摯友劉再復形容他是「中國大陸當代人文科學的第一小提琴手」,實不為過。
不過,李澤厚91歲高齡「走」了之後,在鋪天蓋地的悼念文字中,敏感的傳媒卻「嗅」到了「集體緬懷80年代」的氣息,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周國平的悼念文章〈李澤厚:思想者不懼寂寞〉中寫道:「(我)讀研究生時,李澤厚的大名便如雷貫耳…… 1979年,改革開放伊始,學術界尚是一片空白,李澤厚一氣出版了三部著作,即《美學論集》、《批判哲學的批判》、《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十分耀眼。後兩部是新作,皆大部頭,可知在學術遭廢棄的『文革』年代,這個好學之人並未荒廢學術,一直堅持有主題有系統的研讀,終於厚積而薄發,這個『薄發』,在這裏應該讀作噴薄而發。」
「厚積薄發」的李澤厚,遇上了「噴薄而發」的80年代,產生了非同一般的「化學反應」。「多維新聞」有評論形容80年代的李澤厚「幾乎是獨領風騷,風靡了神州大陸,尤其是在『美學熱』中,他被青年人尊為「精神導師」,在知識界極具影響力。」

言論寬鬆時期 文化難以複製
這篇評論又形容80年代是「最浪漫的時代,而且難以複製」。只因當時的中國內地,「剛剛從文革10年浩劫的泥潭中走出,禁錮人們思想的『兩個凡是』(華國鋒執政時期的口號:「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枷鎖剛剛卸下,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熱火朝天,思想碰撞激盪,言論空間自由寬鬆,封閉已久的巨型社會就像一道洩洪的閘門被衝破,看似平靜的潮水瞬間以不可阻擋的勢頭湧出」。
1949年中共建政後,80年代恐怕是中國內地思想言論自由最寬鬆的時期:北京西單出現了「民主牆」,中美正值「蜜月期」,大量西方經典著作以原文或翻譯進入中國,「剛剛解凍的人們對現實、未來充滿了探索的激情。每個學生都是『問題青年』,都洋溢着一種青春的氣味和對思想的渴望,粗樸而貧乏的物質生活反而更容易催生一種精神的追求」。
當時的大學生,放下了馬列著作和《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聽着鄧麗君的流行歌,如饑似渴地閱讀着《簡愛》、《咆哮山莊》、《浮士德》、《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悲慘世界》、《野性的呼喚》、《戰地春夢》(又譯《永別了武器》)、《戰地鐘聲》(又譯《喪鐘為誰而鳴?》)、《原富》,還有金庸的武俠小說、瓊瑤的愛情小說、余英時的歷史評論、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張五常的《賣桔者言》……。
不過,連李澤厚都會承認的是,到了80年代後期,「理性不足,激情有餘」成為社會時髦的意識。激進的年輕人不滿現實的反叛精神開始顯露,開始像「五四」的前輩那樣否定傳統、否定本國文化,鄙棄「田園牧歌」式的生活,傾慕西方工業文明,擔心不走向「藍色文明」,便會被「開除(地)球籍」。一些人扯得太遠了,論證不講邏輯,學術不講規範,隨心所欲地泛說中外古今,文風膚淺浮躁,尤以1988年央視製作的紀錄片《河殤》和1989年出版關於討論《河殤》的書籍《龍年的悲愴》為代表。之後便是1989年的民運和「六四事件」,寬鬆的80年代便隨之落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