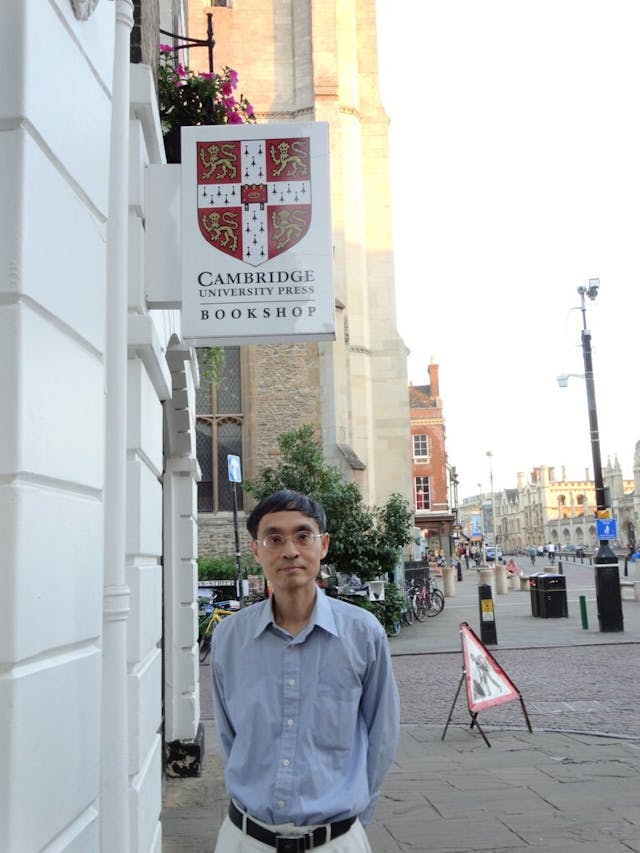你信緣?我信。人跟人,就算歲月逃脫,還能用手抓著的衣袖,這便是「緣分」,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不相識。
我和香港頂尖憲法專家陳弘毅教授是兩種性格、兩個世界;但是,在生命的東南西北,總是碰上、道別、又碰上。他父親是我藝術界前輩,他太太是我的同班同學;不散的筵席。

陳教授香港大學畢業,後去哈佛大學,回港,當了一陣子律師,再到港大,作育英才至今。我要「紀念」這緣分,通過談天,留點文字;他說:「好呀,快來大學午飯,可給你一些珍貴照片!」學長非常愛惜我這學弟;叫他「黃大仙」,也不足說明他的慈悲性格,因為黃大仙還需上香,Albert(我對他的暱稱)是「空氣」先生,沒收費,卻常煩廟堂之事。我和他,經歷太多,兩個男人愛閒聊。
陳弘毅和我吃飯,常互搶「埋單」,禮貌,本該如此。我笑:「你是我的導師!」他淺笑:「為什麼?」我說:「1978年,我考進港大的法律學院,當時,第一個接觸的是『迎新小組』,三人一組,你是組長,教懂我如何適應大學生活。6、7年前吧,我已經『封筆』,你突來電:『橙新聞成立,邀約律師寫網文,我不寫了,你寫吧!』就這樣,筆耕至今;此刻,但覺文字痴纏,既是愛人,又是仇人。」
Albert是吃不胖的,白白、瘦瘦,說話如在圖書館細語,二十分貝:「太多東西沒時間處理,最近,眼睛有些毛病,只好多聽有聲書,書,都堆在地上,看不完。」我苦惱:「唉,患難與共,我耳朵跑出毛病,懶動,想把辦公室搬到床上。」
我們談到2019年至今的動盪香港,都感慨萬端。我說:「衝動,容易被人利用,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後,捲起千堆雪。」
Albert點很多食物,但吃得少:「面對新的未來,我希望年輕人辨析國民的身份,其實民族認同的光譜很闊,你可曾了解國家的河山?風土?文學?歷史?哲學?如只在政治題目打滾,便忽略了中華文化的博大。」我同意:「在殖民地年代,我們的身份是英國屬土公民,卻珍惜民族的身份,許多同學,選擇去唸中國文學、中國歷史、玩中國樂器;大學的旅遊熱點是內地,想看萬里長城和蒙古草原。當時生活困難,但今天人民取得的幸福,特別是脫貧,有目共睹。看扁民族,其實是招引別人看扁自己!」
我問Albert:「世伯陳達文六十年代在政府工作,香港管弦樂團、香港話劇團等是他協助成立的,他是藝術界的功臣,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終生成就獎。小時候,你的精神生活一定很精采?」Albert回想:「哈,我必然學過鋼琴;但是,自己沒有藝術細胞;和其他孩子不一樣的,只是常和家人去看話劇、聼古典音樂會,熟悉管弦樂器和曲目如貝多芬。唸聖保羅男女中學的時候,我唸數理科,到了進大學,父親說法律很實用,我便選讀了。家裏特別的,是藏有大量古典音樂黑膠碟,還有各樣的Hi-Fi器材,像貨場。小時候父母很少帶我看電影,中學時期喜歡的電影Carnegie Hall和War and Peace,都是和同學看的。」
我掩嘴:「小時候,我看電影比看書還多,因為媽媽愛帶我們外出打麻將,但是又不想小朋友吵著,於是給我零錢,拖著弟妹去看電影,我想當導演,但家裏覺得這不是『正常』職業,於是轉為編劇吧,沒想到命運最終是律師。」
Albert對人很好:「還吃什麼?」我失笑:「做律師的好處,是『請別人吃飯,別人請吃飯』,對美食,已失去好奇,吃,只是維持生命的手段吧!」他點頭:「我也不是foodie,肚子不餓,便算。我喜歡看書,但是為了研究,已太多法律閱讀;週末我喜歡看『雜書』或電影,例如科幻、歷史、文學電影,Little Women(小婦人)和許鞍華拍關於蕭紅的《黃金時代》便是其中;雜書如白先勇的《細說紅樓夢》和關於現代德國哲學家的Time of the Magicians。我看電視不多,主要是看新聞、紀錄片。」我支持:「香港人不要怕文化學習,把它看作零食吧,每星期吃一點點。」
我傷心:「我們很幸運,那年代的香港知識分子,許多都精通中英語文,深切了解中外文化。今天,有些人談到中華文化,鄙夷不屑;有些談到西洋文化,又鼻孔朝天,這兩個極端,皆井底之蛙。」Albert感觸:「香港是自由之都,可以吸收中外的文、史、哲營養,我們要好好利用,不應該讓意識形態限制自己,思想應該是客觀、理性和包容的。」我搖頭:「最可怕的,有些家長以子女英語流利為榮,卻不以中文糟糕為愧!」Albert說:「做為中國人,在思想上,應對自己民族的文學、哲學、歷史有良好認識,同時,亦要學習現代西方的思潮和理論,這才是內涵和修養!」我接著:「在路邊,你問人誰是李商隱?魏晉南北朝是哪年代?九流十家是什麼?反應會很可笑!」
我開玩笑:「你長期戍守大學,沉悶?」Albert驚訝:「哪會?港大是一個文化城,如博物館、書店、音樂廳、公開學術講座,太豐富了。有時候,我為外國朋友安排的活動,便是參觀港大,介紹它的建築、歷史、人物;連地鐵站也叫香港大學站(HKU Station),站裏的牆板,更印上港大百年的照片,像校史館。」

我問:「香港的文化生活落後嗎?」Albert回答:「雅文化方面,如古典音樂、人文閱讀、逛博物館等,可能稍爲落後,也許香港人太沉迷於物質生活;但是俗文化來說,一點都不弱,港產片、流行曲、動漫,甚至通俗小說,花團錦簇,這些東西也有文化價值。學校教育方面,過去,過分偏重技術灌輸,如商業和科技,太功利,而忽略人文和倫理教育,包括文學、歷史和哲學。其實,教育最重要的是霍韜晦先生講的『性情教育』和『生命的學問』,學習如何做好人。」
我百感交集:「以前的父母沒有唸書,卻有很多做人的道理,教導小朋友;現在,許多父母都有唸書,但是卻不懂『責己以嚴,待人以厚』,反而一天到晚教小朋友:別人不可以欺負你、你要記得爭取權益,否則,便complain、complain呀!」
Albert揚聲:「來,要不要吃甜品?」我欣然:「一點點。」他接著:「學者洪清田說過現代政治、管治和行政,是以獨立個體及個人自由自主為基礎、建構由上而下的理性多元體制及中立平台。我認爲現代華人應擁抱雙源文化,既學習中華文化的珍貴之處,又通曉西方的現代學論。內地的現代化發展只有數十多年,人民也許未能做到這方面;原本,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人應可以展示雙源文化的力量,可惜,由於政治鬥爭的拖累,這個理想仍成空。但我認為,一國兩制的實驗仍未結束,香港人仍有望成爲中華文化現代化的先行者!」
我激動起來:「學兄,你曾經提到德國的近代史充滿啟發性,因為她從二戰前後、東西德分裂、後來的合併,從血淚中得到教訓;我也希望近年的大事,叫更多香港人長點心,在工作和享樂以外,認真學習中華民族的文、史、哲;內地最近亦啟動『新文科』教育,改善國民的文化水平。」陳弘毅教授最後說:「我衷心希望年輕人,不要只從負面心態去看事情,所謂『反求諸己』,這才是出路。」我點頭:「最近看內地報導,消防已使用無人機,快速滅火救人,國家,在客觀地改善;凡事,在批評後,亦要自我檢討,才會進步。」
飯局裏,滿席都是好吃的菜,而廚房的某對筷子和某個碗,更有緣放在面前;我感受到陳弘毅的高情厚意,又感受到他對香港的擔憂;在愛之深的大前提下,我是「責之切」,而教授是「痛之切」。我問Albert有沒有歌曲想聽?他的笑容像陽光:「《假如愛有天意》,送給我太太。另一首是關正傑主唱的《東方之珠》,送給香港人!」
我和陳弘毅教授,兩種性格、兩個世界;但是在生命的東南西北,總是碰上、道別、又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