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放慢了腳步,生命仍在流動,人可停不下來的,還是得繼續向前走去。
1995年,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第一次用法文寫《緩慢》(Slowness),小說語調是輕鬆的,他說:「沒有一個字是嚴肅的」但一如他一向的作風,調子仍是充塞着嘲諷意味,對人生的嘲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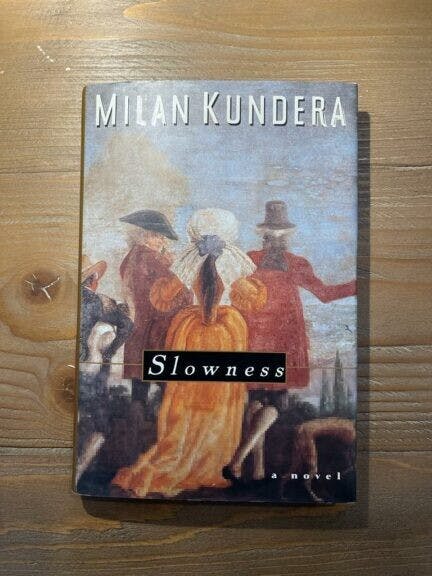
放慢腳步
找出當年他的第一部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那是1984年的英文譯本,喬治.歐威爾的小說也是《1984》啊)。男主角Thomas玩世不恭(只有那樣,他才可以在亂世生存下去?),作者愛說反話,指出”the love of our life maybe light, weight less”。
又嘗試去想想當年看過的同名電影,竟然沒法聯想起什麼來。人的記憶,原來是那麼的不可靠。說當年電影與小說同樣精采,都記不起來了。小說還可以重看,電影呢?
出版家趙家璧寫過《書比人長壽》,說的是寫書的人辭世而去,作品卻可以保留下來。問題是保留下來的文字(結集成書),要是沒有人再去看呢?
不知道會不會再拿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來再看一遍。現在看《緩慢》更有共鳴:「我們每個人都嘗試擺脫平庸,往更高層次走去。」
「我們有此錯覺:我們值得去到更高層次的。」
「當我們要去抗議,反對一些什麼,要是沒有攝影機(記者)在旁錄影、錄音,我們的抗議,誰會知道呢?」
昆德拉就是太愛講道理,不管他講的是《小說的藝術》,還是《可笑的愛情》。當他放慢步伐,不再用文字來諷刺人世的不堪,他還有什麼話要說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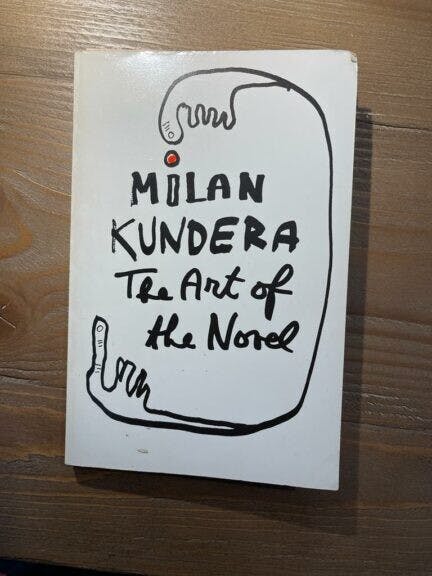
蝸牛和牠的殼
米蘭.昆德拉在The Art of the Novel談及他的小說,與心理學無關。而他創造出來的角色,一如眾多作家筆下的人物,都是不易理解的。而這”Enigma of the self”,正是小說引人入勝之處。
記得有位寫小說的文友對我說:「我筆下的人物,有時候會隨着他的狀態走,不受我控制的。」見我似懂非懂,他說:「我是多麼羨慕昆德拉,他創造出來的角色,有自己的想法、行事方式。作者冷眼旁觀,不會干預他/她們的言行舉止。」
說得太玄妙了。雖然小說角色有自己的生命,但他過怎樣的日子、有什麼作為,作者恐怕也會「推波助瀾」,幫他/她向着某個方向走的吧。
昆德拉是愛說「人生哲理」的。不過,他不是通過小說人物的口說出來,而是作者冷眼旁觀,詮釋人為了自己的存在,作出解釋,盡都是荒謬可笑的道理。作家最愛說一句「人一開始思考,上帝就發笑」。昆德拉下筆的時候,有思考過該怎樣寫的麼?
哲學家海德格說人與世界的關係:Being in the world。昆德拉的詮釋:人與世界的關係,就像蝸牛與牠的殼,連在一起。殼改變,蝸牛也隨着改變。昆德拉的小說角色,有看來是獨立個體,但它像蝸牛一樣,擺脫不了它的殼。
在他的另一個長篇Life is Elsewhere,捷克歷史的改變,男主角Jaromil適應不了,只能一走了之。
他是比《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的主角Thomas幸運,Thomas這隻蝸牛,沒法離開他的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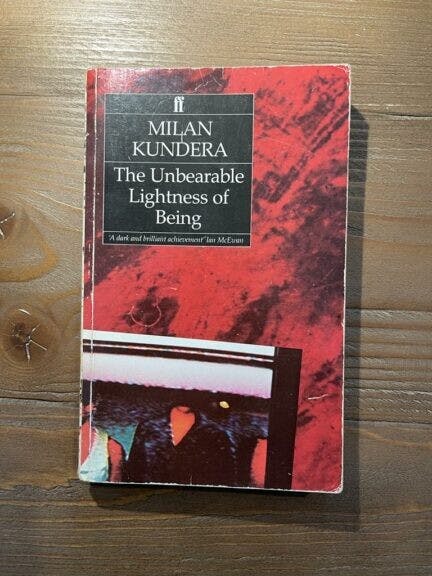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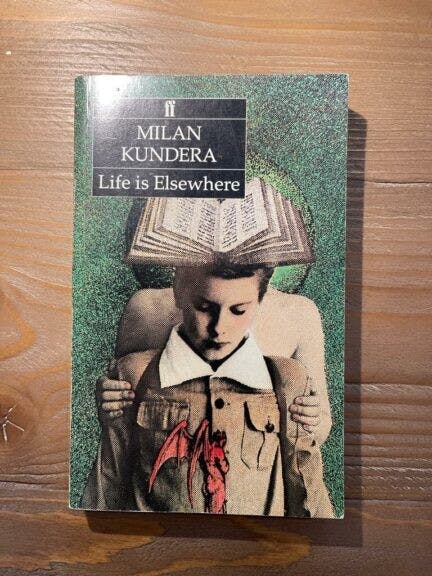
作品魅力
來到米蘭.昆德拉晚年,捷克終於讓長居法國(已成為法國公民)的昆德拉有了個名份,恢復他的捷克國籍,還在他的家鄉為他建立了一間以他為名的圖書館。對昆德拉而言,這遲來的榮耀恐怕他沒法回應(昆德拉圖書館開幕那天,病重的他沒法出席典禮了)。
已經在法國生活多年的他(因1968年布拉格之春事件而流亡法國,1979年寫成的《笑忘書》而被剝奪捷克國籍),要是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一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獲得多次提名,就是沒有獲得該獎項),他會被稱為法國作家,而不是捷克作家。
有說昆德拉的長篇《生活在他方》是作者流亡海外的個人投射。要是這講法成立,那麼其他的作品呢?不也都是流放者的心聲?
昆德拉視自己為國際作家,他不過是長期居住在法國而已。
起初他的作品是用捷克文寫成,1995年用法文寫《緩慢》。離開布拉格已經有26年,可以用法文寫作了。
活在這個世代,我們的步伐應該是快(舞者《緩慢》的主角在台上飛舞,節奏飛快。我們的生活也要如此?而我們的記憶呢?該是快的還是慢的呢)?
對卡夫卡作品情有獨鍾的昆德拉,14歲那年看卡夫卡的《城堡》:”I was dazzled.” 這暈眩感覺自此一直不變。「卡夫卡所講及的人類處境,靠社會學、政治思維語言,皆沒法說得清楚明白。」
就此而言,昆德拉的作品可沒法超越卡夫卡。
原刊於《星島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