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漢學家不少都有一個中文名字,上周六(25日)在美國康涅狄格州家中病逝的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 1936-2021)教授,他的中文名字是他的博士論文導師、明、清史權威房兆楹教授取的,寓意是「景仰司馬遷」,即是以「太史公」為榜樣,「究天人之際,通古今次變,成一家之言」,反映了老師對學生的期許極高。
從史景遷教授日後在西方漢學界的表現看,並沒有辜負老師的期許,他在耶魯大學任教40多年,講座一直受歡迎,許多著作都成為研究中國的「經典」,例如《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1990)這本書,厚達870頁,從17世紀明朝鼎盛時期,寫到1989年的「六四事件」。這部洋洋巨著後來登上了《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對於史景遷教授的著作,筆者印象比較深刻的是《太平天國》(God’s Chinese Son :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of Hong Xiuquan),從書名便可看出,作者的旨趣主要集中在「上帝的中國兒子」洪秀全身上。
洪秀全、馮雲山1840年代在廣西傳教,建立「拜上帝會」;1851年在金田村發動對清廷的武力對抗,即「金田起義」,一直到1864年洪秀全身死,「天京」(南京)失陷。這段歷史,許多中國人並不陌生,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就有一幅以「金田起義」為題材的浮雕。

由於中國近、現代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和毛澤東均推崇洪秀全,研究太平天國,多年來都是中國學術文化界的「顯學」,最著名的研究者包括歷史學家羅爾綱(1901-1997)、茅家琦(1927-)等。不過,史景遷筆下的太平天國,跟傳統的歷史敍述有些不一樣。
寫歷史重視「講故事」和寫作技巧
正如史景遷在《太平天國》一書的〈序言〉中,開宗明義表示:「本書無意描述太平天國運動完整的歷史……我主要關注洪秀全的心靈,試圖盡可能地理解這位不尋常的人物,何以能夠在如此漫長的歲月中,對他的國家產生如此令人震驚的影響。」作者從宗教入手,探索洪秀全的心路歷程,講述一個不一樣的太平天國故事。
首先,贈送基督教宣傳小冊子《勸世良言》給洪秀全的,是作者梁發嗎?史景遷經過考證,認為是美國傳教士史蒂文斯(Edwin Stevens)於1836年贈書給洪秀全的。
洪秀全只讀過這本《勸世良言》,便自認見到「天父、天兄」,邊傳教,邊造反,一直打到「天京」稱「天王」了嗎?史景遷認為沒這麼簡單,事實上早在太平天國初期,西方人認為太平天國運動是《聖經》啟示的結果,視太平軍為「基督徒」,傳教士亦不只一次面見洪秀全,贈他《聖經》。洪秀全本人也有刪改、批註《聖經》,說明他有讀過某些版本的《聖經》,只不過太平天國「拜上帝」的方式摻雜了「民間信仰」,即內地史學家也指出的,「東王」楊秀清玩「天父」上身;洪秀全妹夫、「北王」蕭朝貴玩「天兄」上身,這便有點「神打」的味道了!
停印《聖經》 非因洪楊之爭
後來,太平天國中止了出版《聖經》,史景遷認為,起因不在洪、楊之爭,而是楊秀清與英國來使以書信往來的一次「宗教辯論」,英人引用《聖經》,逐點反駁太平天國的「教義」,這令楊氏意識到《聖經》對其「教義」的威脅,遂以「天父下凡」的名義宣布《聖經》「錯訛甚多」,後由洪秀全親自完成了「修訂」《聖經》,在在都說明,馮雲山、洪秀全並非只讀了宗教小冊子便去「傳教」,而外國傳教士本來也有意招攬洪秀全做「外國代理人」,但洪楊的任意詮釋教義,加上後來洪楊內訌,諸王互相攻殺,「翼王」石達開出走,外國人便對太平天國徹底失望了。
太平天國運動造成千萬生靈塗炭,《太平天國》一書援引史料,寫到「天京」即將城破,城內民生之凋敝,令人掩卷三歎;寫到洪秀全死後,「幼天王」洪天貴福的命運,令人不忍卒睹。有人說,大清之亡,實不自1894-95年的甲午戰爭始,實在由太平天國運動起,這場歷時10年的造反,盡顯滿清「八旗兵」的無能,遂使湘淮地方武力壯大,埋下日後軍閥割據的伏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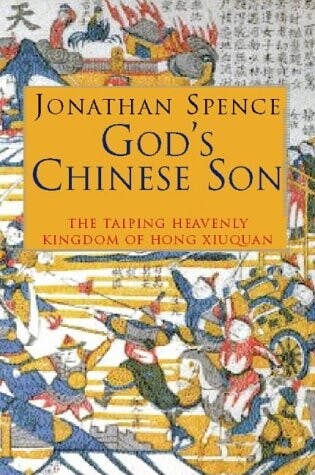
中文間有誤解 無礙史識發揮
史景遷共有十多本著作,或許不能說每一本都是「壓卷之作」,但從《太平天國》可看出,這位歷史學家無疑是一位說故事的高手。故事說得好,學術水平高,一樣有考證,一樣有獨到的見解,這便是史景遷。
在同輩的漢學家中,史景遷的中文能力或許未臻一流,有論者指出,在《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一書中,史景遷間或誤解了張岱原文的意思,比如張岱自稱「書蠹詩魔」,自嘲讀書、讀詩像着了魔般,史景遷卻理解為「書使他中毒,詩使他迷惑」。還有「莫逆」一詞,中國人都知道是指「莫逆之交」,史景遷卻誤以為「平定叛逆」。
不過,把大學裏枯燥的歷史,變成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物故事,除了史景遷,筆者只想到台灣的歷史小說家高陽,但高陽寫的畢竟是小說,而史景遷卻是以說故事的手法寫敘事史,因此被譽為「最會講故事的西方漢學家」,這大概便是金耀基教授強調的「史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