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生命旅程中,順境的歡悅與逆境的惆悵交錯;面對戰爭和政治運動的殘酷,則有太多的無奈,或也有死裏逃生的僥倖。
許燕吉就是死裏逃生的一位,她嫁給文盲老農,是陳年故事,早寫入自傳《我是落花生的女兒》(湖南人民出版社)。她的故事,近期又成為一些網絡平台的熱話題:從「上山下鄉」、許燕吉故事,到反思毛時代(1949—1976)特別是毛文革(1966—1976)。
今年是「上山下鄉」結束40周年,也許反思者帶出許燕吉故事,以解釋反思的「必要性」;另一話題熱起來原因,是圖書發行界傳出消息,香港書展如能在12月舉行,她的自傳將參展。(編按:貿發局宣布書展延至2021年7月舉行)
作家落花生 港大名教授
筆名落華生、落花生的許地山,是「五四」(1919)後新文學的代表作家,與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茅盾)、葉紹鈞等發起文學研究會,並在《小說月報》發表作品。代表作有散文集《空山靈雨》、小說集《綴網勞蛛》和論著《道教史》、《印度文學》等。
夏志清(1921—2013)教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讚賞文學研究會的寫實主義,提到許地山的短篇小說〈玉官〉和〈春桃〉。又說,與同時代的作家「不同的一點」,是對宗教的興趣,他關心「慈悲或愛這個基本的宗教經驗」,「給他的時代重建精神價值上所作的努力……是一種苦行僧的精神」(中大版71、72頁)。
許地山生長於官宦之家,父許南英(生於台灣台南)在清末當過兵部小官主事,後任台南團練團統領、廣東三水縣知縣(縣長)、電白縣知縣。
許地山為基督教徒,由教會資助入北平燕京大學,後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牛津大學修碩士學位,返國後任教於燕京大學。1935年,胡適(1891—1962)推薦他當了港大中文系教授。學生有後來成為名作家的張愛玲(1920—1995)(註1)。
許地山交遊廣,史學家陳寅恪、陳垣及其子陳樂素,劇作家熊佛西、儒學專家梁漱溟、畫家徐悲鴻等,都是好朋友。許燕吉少年兒童時代的友伴,多為他們的子女。
1941年8月,許地山病故,同年12月日軍打入香港。第二年,許燕吉隨母親北返逃難。
她的母親周俟松,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數學系(1928),曾在香港銅鑼灣道培正小學任教。1950年代,在南京當中學副校長、數學教師。

許燕吉北返 受肅反牽連
許燕吉離開香港後,在貴州貴陽、四川重慶和南京念書。
1954年,她畢業於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系,分配到河北石家莊奶牛場。
1955年,毛把胡風事件擴大為肅清反革命(簡稱肅反)運動。當時她在河北農科所工作,被列為「敵嫌」審查。原因是她在南京讀中學時,參加過天主教活動,又因一同事的告密而增加「暗藏反革命」之疑。
1957年反右,她又遭批鬥。1958年初,定為反革命、右派分子,後判刑六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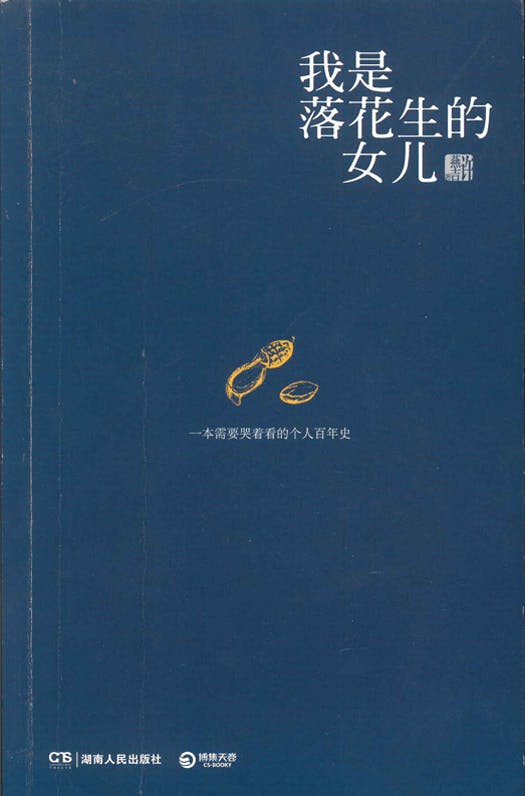
各睡一個炕 性慾望很低
1968年,毛發起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在1950年有小規模的「上山下鄉」),城市無業可「就」的知識青年(包括刑滿出獄知青),都下鄉當農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許燕吉到河北農村勞動,後來轉到陝西武功縣楊陵鎮官村,嫁給大她十歲的文盲農夫。
她的自傳寫道:
「我就睡到小燒炕上。老頭子的炕很窄,我也不願挨著他睡。……燒鍋的時間短,睡燒炕不算太熱。老頭子打光棍已十年,年歲也臨半百,對性的欲求淡漠,很少到燒炕上來騷擾。我們真是做到互不侵犯,和平相處。」(404頁)
1979年,她獲平反,回南京在省農科院工作,後定為副研究員,丈夫也獲「農轉非」(農村戶口轉為非農村戶口),有南京市戶口,並在農科院養羊,2006年85歲時病亡。
因許地山的社會關係,她成為統戰對象,當了「台聯」的理事。2014年初因癌症亡故,享年81歲。

遭告密受疑 鐵窗女囚苦
她的自傳「前言」曰:
「我生活在動盪的歲月,被時代的浪潮從高山捲入海底;國家幹部變成了鐵窗女囚。……國內的同齡人幾十年來也未見平坦風順,只是我的人生被扭得多幾圈而已。」
在封底,還印上她的感慨:「歷史,……更多的是無數普通人的辛勞、痛苦和隱忍,那是歷史的傷口,也是歷史的真實。」
她正是道出「歷史的傷口」,再現「歷史的真實」。從1955年的胡風事件和「肅反」,1957年的反右,到1966—1976年的毛文革,她都是「運動員」,即政治運動中受懷疑者或被整者;也是1958—1962年大飢餓的受難者(註2)。
1955年牽扯到「反革命」罪,是因為農科所的同事告密,向黨委幹部提起她「說怪話」(發牢騷)。事後,告密者有點內疚,向她解釋什麼,她回答說:「話是我說的,你沒像別人給我編造什麼,……並不怨你。」(204頁)
女牢限尿令 憋得冒冷汗
書中對暴力的折磨、人格尊嚴的喪失,有較多的描述。她寫看守所的「限尿令」:
「罰人站、扣人糧,最厲害的是讓人憋尿。女犯放茅一天只兩次」;
「早餐總是稀糊糊,憋得人左搖右晃頭冒冷汗,真是一種特殊的體罰。」(241頁)
對於大飢餓,她也着墨不少。她提到弄點醬油摻水喝,讓肚子暫時解餓;也寫吃爛紅薯的滋味:
「對著那黑了一半的紅薯,我沉吟了四五分鐘:吃吧,它苦不說,還有毒,不吃吧,就什麼也沒有了。狠了狠心,我把那黑疤病的紅薯硬吞了下去……當時的斟酌抉擇令我終生難忘。」(287頁)
死亡邊緣者 六粒救命豆
她不是只寫暴力和飢餓,也寫監獄裏難得的一點「人情味」、一絲令人意外的「人道主義」:賈書記找到糧食局長看病殘的囚徒,要他援助一些黃豆。她寫道:
「自此,浮腫嚴重的和乾癟的每天可得到6粒黃豆,這是賈書記給爭來的救命豆。」(290頁)
在自由、有飯吃的社會,聽到吃黃豆要數幾粒,每天能吃六粒竟是「恩典」,自有「謊謬」之感。
這六粒,不是人人有份,僅限於死亡邊緣者;這六粒,未必真能成為「救命豆」,卻體現有人尚存一點人性。
儒家經典《孟子.公孫丑》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為囚徒「爭取」六粒黃豆,正是惻隱之心催生的義舉,是黑牢裏罕有的一絲人性之光。許燕吉記下了這種事實。
註:
2.〈大飢餓(1958—1962):3000萬人餓死的悲劇〉
本文原題〈港大教授女兒 嫁給文盲農夫〉,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站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