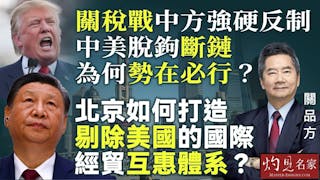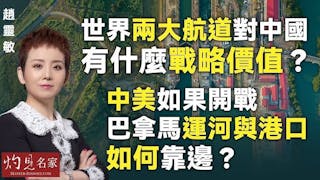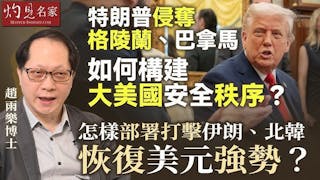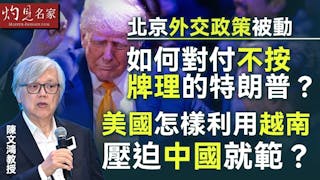從法律上來說,1997年回歸之後,香港已經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也就是說,香港已經和大陸統一。但是,法理上的統一,並不是說統一的過程完成了。相反,香港近年來不僅僅在政治改革問題上分歧巨大,和大陸所希望的相去甚遠,更為嚴峻的是在發展出一種獨立力量。這種獨立力量儘管是絕少數,但卻不可以掉以輕心。在全球化和社交媒體時代,如果處理不好,這些所謂的少數人的問題就會隨時演變成高度國際化的問題,或者說,少數人的獨立運動可以為整個國家製造出顛覆性錯誤。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必須花大力氣把香港問題解決好。
1997年,香港的順利回歸並不容易,表明回歸之前有關香港的工作做得很好。回歸過程中,也遇到了巨大的困難,但中國方面克服了所有這些困難而實現了順利回歸。這裏有很多因素,但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香港回歸始終是最高領導層的最高議程之一。也就是說,中央政府是以一種高度集權的方式來處理香港回歸的問題。不過,九七回歸之後到今天,香港出現了很多的問題,並且問題的複雜性愈來愈甚。實際上,香港已經成為中國的一大挑戰。為甚麼會演變成現在這個樣子?這裏,在很多方面的因素是可以考量的。
回歸之後的一段時間裏,香港問題很快在最高領導層的日常議程中消失了。原因很簡單,很多人認為,九七回歸一結束,香港問題就解決了。香港問題從最高領導層的議程中拿掉之後,馬上就落到了各級政府和官僚手中,也就是說,開始用一種分權的方式來處理香港問題。但問題馬上就出現了。權力被分散在不同的官僚機構手中,而官僚往往是不具備解決香港問題的能力的。 2003年,香港數十萬人上街遊行,抗議特區政府。這個之後,香港問題再次回到了領導人的議程。但即使這樣,很多問題還是解決不了,並且在惡化。
香港回歸後沒有「去殖民地化」
大陸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不過,這麼多年下來,大陸和香港對一國兩制有了全然不同的解讀。大陸方面強調的是一國之內的兩制,但香港方面尤其是民主派方面則傾向於強調兩制而非一國。也就是說,香港人的中國意識愈來愈淡薄,甚至完全沒有中國意識。發展到現在,一些香港人不僅不認同中國,而且以做中國人為恥。儘管這部分人是少數 ,但這部分少數是具有話語權的少數,深刻地影響着香港的整體。這種強烈的非中國認同,甚至反中意識是目前香港問題的核心癥結。出現這種情況更表明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出現了問題, 如果不是失敗的話。人們至少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首先,香港回歸之後沒有經歷一個「去殖民地化」的過程。香港成為英國的殖民地160多年,但回歸之後,甚麼東西都原原本本地被留下來了。這種主權移交方式當時被稱頌,但現在證明是個大問題。二戰之後,原來被殖民的國家出現一波反殖民地運動,民族國家紛紛從殖民地宗主國那裏獨立出來。回顧歷史,人們不難看到至少有三種「去殖民地化」的方式。
第一種表現為簡單的更換統治者。在反殖民地統治過程中,運動的領導人往往也是接受西方教育的。他們通過反殖民地運動,把作為統治者的殖民者趕跑了,而自己變成了統治者。而在制度層面,他們不僅往往繼承了原來殖民者建立起來的制度,而且經常把原來的殖民者不曾實行的西方制度也引進來。這種方法表面上「去殖民地化」了,實際上反而強化了殖民制度。這種方式並沒有很成功的案例,失敗的案例倒不少。今天很多發展中國家擁有原來殖民地宗主國所擁有的所有制度,包括憲政、多黨制、三權分立、自由媒體等等,但所有這些制度只是作為擺設,並不能發揮真正的作用。
第二種是徹底更換制度。一些國家在反殖民地主義之後,完全脫離和改變了原來宗主國所遺留下來的制度,而實行一套不同於殖民制度的制度體系。一些國家返回到殖民地之前的更為傳統的制度體系,例如亞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而另外一些國家則採用了另外一套「進口」的制度體系,例如那些實行共產主義制度的國家包括越南、古巴,就是這種類型。
第三種是通過制度改革,在去殖民地化的同時保留殖民地制度中一些有效的制度,和本地社會的一些制度有效結合起來。新加坡是個很典型的案例。在獨立之後,李光耀所領導的新加坡可以說是採用了自主創新模式,有機地整合了東西方最優的制度和實踐,形成了自身獨一無二的制度體系。李光耀自主創新的巨大能力來自其深懂歷史和世界事務。他不僅知曉歷史上不同帝國政治秩序的優劣,更知曉他那個時代世界上各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優劣。他所擁有的「工具箱」(知識體系)使得他能夠把他認為是最優的制度和實踐結合起來,成為自己的制度實踐。
愈是年輕愈反大陸
香港在回歸之後,沒有出現任何形式的「去殖民地化」的努力。這使得香港的體制很難適應大陸的體制,也就是說,一國之內的兩種制度之間的矛盾過大,很難互相適應。原來人們認為 ,大陸的體制也在變化,並且會變得和香港的體制差不多。但現在看來,大陸體制的變化並沒有往香港的方向走。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兩個體制要互相適應,就需要香港的體制有所變化。 這種變化並不是說香港的體制要完全變成大陸的體制,而是說香港的體制至少不會直接去挑戰大陸的體制。但是,在沒有任何去殖民地化的情況下,香港和大陸的體制變得愈來愈格格不入。 當兩種體制的互動愈來愈多的時候,衝突的機會也增多。
再者,回歸之後,香港社會具有了政治空間。在港英時代,香港沒有政治空間,一切政治歸於港英當局,香港所有的只有行政。有了政治空間就表明,香港人具有了政治話語空間。因為沒有去殖民地化,新發展出來的話語必然是針對中國大陸的。香港話語不僅要突現香港與大陸的不同,而且具有很大的雄心要改變大陸。香港的民主自由話語的發展就是如此。要意識到,具有濃厚香港地方意識甚至反中意識的是香港九七回歸以來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愈是年輕人愈是反對大陸,這個事實本身就需要大陸有關方面深思。
國家認同教育推行不當
在強化一國的方面,大陸也並不是沒有任何努力。但這些努力都出現了重大問題。第一,在推行國家安全法,即23條方面不當。香港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通過23條非常合理。但問題是如何推行。現在看來,推行方式缺乏專業精神。大陸推行的是整體推行方式,即通過23條。在沒有去殖民地化的情況下,香港人的反對是可以預期的。不過,如果採用「分解方式」,效果可能會好得多。例如,香港可以對收取外國資金出台法案或者條例。包括西方民主在內的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法律,這樣的法律並不難制訂。
第二,國家認同教育推行不當。香港回歸中國之後,早就應該推行國民教育。在任何國家,國民教育是去殖民地化的一個最為關鍵的方法。但這方面遲遲沒有作為。直到後來問題變得嚴峻起來,才這樣去做。不過,做的方法又過「左 」。把一大堆很左的東西放在一起變成了國民教育的材料,並且強行推行。這種方法即使在大陸也會遇到巨大的阻力,更不用說是長期接受殖民教育的香港了。國民教育引起了港人的強烈反彈,這不難理解,失敗也是預期之中的。
香港體制的諸多矛盾
其次,香港的基本政治體制設計存在很多矛盾。在港英時代,人們說「行政吸納政治」。這種說法當然不能成立,並且具有很大的欺騙性。港英時代不是行政吸納了政治,而是根本就沒有政治。政治歸於英國,香港人並沒有任何權利參與政治。但回歸之後,香港不僅出現了政治,而且政治是屬於港人的。同時,香港也發展出了現代政黨政治。在這樣的情況下,如同所有的政黨政治,政治首腦必然要由政黨政治產生。不過,很顯然,香港並沒有理順政治與行政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政黨政治和特首之間的關係。作為政治首腦,特首並非由政黨產生,而是通過另外一個政治途徑產生的。在立法會中,特首要面臨通過政黨政治產生的議員,而特首並無任何政黨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特首的合法性就成為大問題。
再者,香港的政治是誰的政治呢?這個問題也一直沒有搞清楚。就立法會來說,有地區直選議員,也有功能界別議員。兩種議員都是政治過程產生,但政治的含義是不同的。香港很多人對功能界別議員很有意見,這不難理解。功能界別實際上有其特殊的政治功能,主要是協調不同社會階層的需求。但直到現在,功能界別並沒有多少民主,其所產生的議員並沒有多少民主味道。 如果功能界別也引入民主,那麼情況就會不一樣,就會產生美國上下兩院的情況。
再次,如同大多數國家和地區一樣,香港也面臨資本的問題。全球化造就了社會的分化和巨大的收入差異,這是一個普遍現象。香港的經濟結構本來就是少數利益集團主導的。隨着大部分製造業轉移到大陸,而新的產業並沒有發生,經濟結構的畸形性愈來愈顯著。全球化儘管也給香港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但這些利益都被既得利益所獲取,普通人民並沒有帶來多少的好處。 對民眾來說,無論是收入差異還是社會分化,都是政府的責任。社會對抗政府成為不可避免。儘管資本要負很大的責任,但社會沒有辦法來對抗資本,因為資本是可以跑掉的,因此民眾就把矛頭對準了政府。大陸在這個過程中也儼然成為了犧牲品。每當香港出現嚴重的經濟問題,大陸方面就通過各種政策例如更緊密的夥伴關係、自由行等等輸送經濟利益。不過,同樣,這些經濟利益大多數走向了少數既得利益集團。這種結果也導致了香港很多人的不滿。
今天,無論從意識形態還是從政治立場看,香港呈現出了兩個極端政治,一個是親大陸的建制派,或者左派,一個是親西方的反建制派,或者民主派。因為恐懼於香港問題的惡化,大陸就只好全力支持左派;同樣,因為恐懼於被大陸化,民主派就拼命抵抗,並和西方靠近。這種對立的狀態愈來愈嚴重。
更為嚴重的是,香港也很快發展出少數獨立力量和獨立話語,要從中國大陸獨立出去。一些海外香港人也開始加入獨立力量。儘管在大陸看來,這是匪夷所思,但這是確實的事情。 這種對立的情形一直下去,獨立的力量會繼續擴展。儘管獨立力量是很少數,但這些關鍵的少數可以通過國際化而發出巨大的聲音,不斷製造政治危機。直到今天,人們只看到種種反應性的應付危機的方法,各方僅僅糾纏於例如政改那樣的細節問題,而看不到具有大格局的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這使得人們非常擔憂香港的未來及其一國兩制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