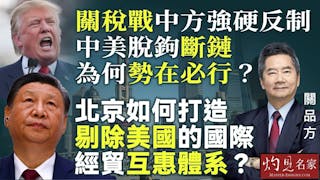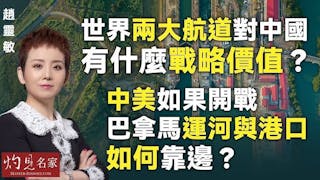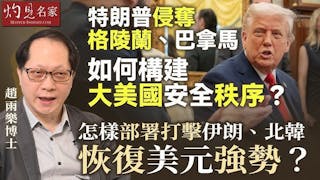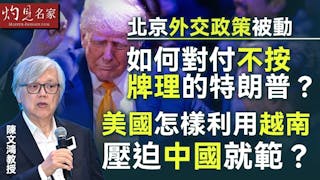在歐洲,法國政治歷來被視為具有先驅性和象徵性,其政治變遷也遲早會影響到其他國家,甚至會在其他國家發生。法國最近發生了甚麼變化呢?極右派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在快速崛起。國民陣線成立於1972年,鼓吹經濟上的保護主義,社會上的保守主義和政治上的民族主義。成立之後,國民陣線一直活躍在法國政壇上,包括參加2002年的總統競選,差點執政。到今天,國民陣線已經成為法國最大的政治力量。
近來,有幾個因素使得國民陣線再次引人注目,也使得人們開始擔憂西方政治的未來。首先,《沙爾利周刊》遭恐怖主義攻擊後,國民陣線意識形態的正確性似乎再次得到了印證,即反對全球化和開放的移民政策。國民陣線認為法國正在遭受穆斯林的攻擊。第二,在外交上,國民陣線認為法國應當退出歐元區,美國不可靠,主張和俄羅斯靠攏。第三,最為顯著的是,這樣一個極右政黨,開始主張原來由極左政治力量才提倡的勞工政策。至少在意識形態上,國民陣線試圖整合極右和極左的力量。這些因素使得國民陣線成為今天法國民眾支持度最高的政黨。
儘管國民陣線能否在法國執政,及其執政後會否把它的意識形態轉化成為實際的政策等,還都是未知數,但人們必須對即使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變化給予足夠的重視。在亞洲,意識形態在政黨政治中並不重要,亞洲的政治力量往往是先有利益,再去找意識形態來論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但歐洲則相反。
近代以來,歐洲政治就是階級政治,各國政權一直在左右派政黨間轉換,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國民陣線使人驚訝的地方不是因為其極右,而是這個極右政黨試圖整合極左的政治力量。希臘、意大利、匈牙利等國也已經出現類似的發展,即左派政權吸納右派力量。在歐洲政治史上,希特勒時代的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就是這樣一種極左和極右相結合的政治力量。沒有人會說,歐洲會重演從前的歷史,但這些政治現象的發生,應當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和思考。
左中右都無法解決問題
二戰後,左派佔據歐洲政治的舞台。戰後經濟迅速復蘇,福利制度急劇擴張,隨之膨脹的便是管理福利制度的國家官僚機構。到了1980年代,左派政治難以為繼,政治往右轉。英國的戴卓爾主義是右派政治的象徵,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政策。戴卓爾主義很快擴展到大部分西歐國家。不過,右派政治也同樣產生了很多問題。到了貝理雅的時候,提倡「第三條道路」,既不左、也不右的中間道路。但近年來的政治發展,表明了極左和極右力量趨向結合的趨勢。如果這個趨勢成為政治現實,必然對歐洲乃至整個西方政治產生巨大的影響。
人們可以把這種趨勢稱之為極端主義。極端主義的回歸絕非只是這些政治力量的操作,而是反映了歐洲乃至西方政治的深層問題,也就是今天的西方民主所無能解決的問題。西方政治面臨的困境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來探討。
第一是全球化對西方的影響。1980年代以來,西方是全球化的主體和推動者。這一波全球化主要由資本驅動。有幾個主要因素有效推動了西方資本的全球化。首先是西方的產業升級,一些產業需要轉移到其他國家,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其次是福利制度,西方實行高稅收政策,資本試圖通過「走出去」來逃避本國的高稅收。再次是在私有化路線下,西方各國放鬆了對本國資本的管制。同時,一些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國開始實行開放政策,也使得西方資本能夠在海外尋找到巨大的空間。
全球化在為西方國家帶來了大量財富的同時,也導致了收入差異的加大。那些能夠參與全球化的人口(主要是資本)獲取了最大量的利益,沒有能力的人口則成為受害者。同時,全球化也為歐洲國家帶來了大量的移民,包括穆斯林人口。無論是收入差異意義還是種族意義上的社會分化,都給今天的西方社會帶來了無窮的社會和政治問題。
第二是產業結構的變化。首先是產業轉移問題。舊的產業轉移出去了,但沒有新的產業替代。歐洲曾經在世界製造業中佔據重要地位,但今天除了少數幾個國家(德國等),製造業已經不再是歐洲的主要產業。製造業的衰退深刻影響了西方的就業結構。大量人口尤其是年輕人的失業,是西方社會又一個影響社會政治穩定的大問題。其次是產業結構本身的變化。很多國家的產業向金融業和信息產業發展,它們不能產生中產階級。再者,由於技術的進步,一些傳統上能夠為中產階級提供工作機會的產業,也大量縮減工作機會。這使得原來的中產階級處於非常不利的地位,他們的工作要不被資本所「剝奪」,要不被掌握低端技術的底層(包括外國工人)所「剝奪」,原來的生活水準難以為繼。
第三是西方民主制度在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失衡。這可以用簡單的算術來說明。今天的大眾民主最直接的表達就是「一人一票」,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一人得一份(福利)」。但從「一人一票」到「一人一份」的轉換需要條件。如果一人要得一份,前提就是一人需要貢獻一份;如果一人不能貢獻一份,體制就不可持續。矛盾顯現於「一人一票」的民主要保證「一人一份」,因為政治人物必須這樣做,否則就得不到選票,掌握不了政權;但是,「一人一票」根本不能保證一人能夠貢獻一份,或者說,「一人一票」的民主根本就不包含一人必須貢獻一份的機制。這樣的民主難以持續。
在大部分時間裏,西方實行的是精英民主,大眾民主也只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事情。在精英民主時代,選舉和被選舉權都是有財產限制。誠如馬克思所言,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精英民主主要表現為政治階級和資本階級之間的權利分配,後來這種權利才逐漸擴展到全體人口。隨着選舉權的擴展,社會權利,即福利政策,也得以擴展。西方早期的福利政策是極其保守的,主要是為了保護資本利益,通過保護社會而達到社會穩定,因為資本的運作需要穩定的社會環境。德國俾斯麥時代出台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保障政策,就是典型的例子。現實地說,社會政策就是富人(往往是資本家)出錢買穩定。
但是隨着民主的擴展,人們對社會政策性質的看法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到今天,社會政策被普遍視為是人生而有之的「權利」。這種權利觀的普及對西方民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果要贏得選民的支持,政治人物就必須向選民承諾高福利。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曾經批評,西方的這種民主是「福利拍賣會」,誰出價高(提供高福利),誰得票就多,誰就可以掌握政權。這就改變了政治和經濟之間的平衡。在精英民主時代,因為政治人物大多為資本所推薦和支持(即馬克思所說的「國家是資本的代理」),他們必須考慮到政治和經濟之間的平衡。但是,在大眾民主時代,儘管資本的支持還是很重要,但政治人物最重要的考量變成了選票,也就是選民。這使得政治人物急劇向選民傾斜,而對資本不利。
既有福利制度難以為繼
在不能實現一人貢獻一份的情況下,如果資本願意多貢獻幾份,讓那些沒有能夠貢獻的社會成員分享,體制還是可以持續下去。但如果資本不願意這樣做,體制就會遇到麻煩。實際上也是如此。在「一人一票」的體制下,人們往往把自己所擁有的權利視為當然,而且對權利的要求也無度。誰來貢獻一份呢?只有資本才能這樣做。問題在於,資本的本性並沒有改變。資本不願意看到政府通過高稅收,把自己的財富轉化成為社會成員的權利。同時,資本是有能力逃避這種情況的。資本的全球化就是其中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在全球化時代,政治和社會是不能流動的,資本卻可以,這使得三者之間更容易失衡。政府如果實行高稅收政策,資本就會跑掉;但如果減少福利,依靠福利而存在的社會就會不滿,政府就沒有合法性。如何維持福利呢?西方有幾個通用的辦法,包括向中產階級徵稅、債務(向老百姓、外國借錢)、犧牲未來(照顧有選票的老人而犧牲沒有選票的年輕人)等。但這些都不是長遠之計。向中產階級徵稅已使得他們苦不堪言,西方各國都面臨中產階級危機。大肆借債已使得西方各國債台高築,到了危險的邊緣。通過犧牲年輕人向老年人買選票,更使得西方年輕人感覺到毫無前途,這也是今天西方年輕人反建制的重要因素。
即使沒有全球化,「一人一票」體制也難以為繼,因為這裏還有資本的動機問題。如果資本所得大都被政府用在福利,依靠福利而生存的社會階層(或者「懶人」)便會愈來愈大,資本所有者就不會有動機去創造財富。
西方的「一人一票」制度發展到現在,產生了如此深層的問題,已經需要引入激進的改革。但談何容易?儘管西方人知道問題出在哪裏,也知道如何改革,但就是解決不了誰來改革的問題。大眾民主很難產生有效政府,因為只要福利和選票掛鈎,通過選舉產生的政府,將沒有任何能力來做犧牲選民利益的改革。
歐洲極端主義的崛起,既是對這種政治現狀的不滿,也是為了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裏,本質性的問題就是要產生能夠解決問題的有效政府。歷史上,只有強人政治才能解決問題。世界各地都是如此。但強人政治又具有很大的危險性,希特勒的國家社會黨就是明證。如此看來,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再次進入很不確定的時代。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