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科幻小說作家譚劍、伊格言、韓松討論了不同的城市地區給科幻帶來不同的靈感,人類是否本身就生活在虛構之中,也許未來AI會與人類結合等等妙趣橫生的話題。以下是講座實錄,分兩篇刊出,第一篇在此,本文為第二篇:
為你謀篇布局的可能不是人類而是AI
譚劍:我很好奇,你們寫作前會不會準備大綱或者畫圖?推理小說的故事結構跟科幻小說不一樣,推理小說講究的是謎團/詭計,整個故事就是一個破案的故事。福爾摩斯那樣最後叫所有人都在場把真相說出來,這都已經是非常古典的做法。現在最後的真相可能是幾個人交錯講出來的。這樣整個故事的設計一定要想好,如何埋線,如何揭開。我自己會用mind map去做鋪排,不然我無法寫故事。我是工程師的腦袋,一定要設計好架構,才能把血肉填進去,比較接近推理小說家的想法。
你們兩位,背景很不一樣,寫出來的故事結構和我的也很不一樣,所以,你們創作的過程是怎樣的?
韓松:我沒有畫圖,也很想畫圖,但主要是沒有時間去結構這個東西。我就是一點一滴地,寫到什麼地方算什麼地方。另外我還有個觀點,世界是不確定的。任何一種事情,未來也是難以確定的。就讓他自然地發展。即使給它設定一個圖,可能科幻小說發展到最後,也會把它給打破。科幻的力量本身在那個地方,它會打破最後設定的的線路。
譚劍:其實我自己畫圖,就算很精準,最後可能只有五成/七成按照了預定計畫,不會完全相同。因為寫作時進入了角色,就會發現角色和作者自己想事情地方法不一樣。我覺得我應該讓那個角色有他們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決定,最後我就讓他帶着我走,而不是完全控制它。
所以伊格言你又怎麼樣構思你的故事?
伊格言:剛剛聽譚劍這樣講,我真的很想抱抱他。真是辛苦了。因為我跟譚劍完全一樣。
我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噬夢人》有27萬字,我邊寫邊做筆記。這個筆記就像譚劍說的mind map,去分析裏面有什麼結構/謎團/詭計,如何拆解,牽涉什麼任務和細節。整個筆記的字數是8萬字。8萬字,都可以出本書了。我每天都在往前對,因為科幻小說牽涉到年代的問題,可能要設定什麼年代有什麼樣的科技,這個時間線不能搞混。所以後來也畫了一張年表,筆記愈長愈多,非常可怕。
小說的主幹和結局,可能要事先想好。但事實上你寫下去會變得不一樣,到最後可能六成或七成跟你的計劃一樣,會產生變化。我就是從這樣子的一個過程當中,就體會到那種寫軌跡/諜報的作家的智性的辛苦和愉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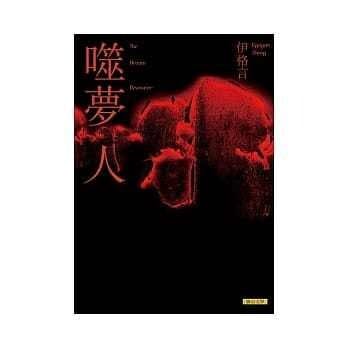
譚劍:我們都會寫筆記,我們稿子交給編輯之後,編輯也會寫,有時採訪我的記者也會畫mind map,他們畫得複雜的圖,我自己看了都嚇死了。我想問,你們有沒有用特別的軟體畫時間性或者做筆記?
伊格言:我覺得的確科幻小說家才比較會這樣想,我自己是寫純文學小說出身的,我很難想象台灣的純文學小說家做這種事情。寫《噬夢人》是,mind map軟體還沒有那麼多,最近也有一些年表軟體,我都花了一段時間研究軟體,不過後來沒有用。我還是習慣比較單純的文字筆記。
韓松:我自己沒用,但是我周圍好多科幻作家現在都在用軟件設計小說,包括時代年表、故事的架構或走向。科幻小說是個現實主義的文學,哪怕是描寫一個虛假的世界都特別的逼真,跟真的一模一樣。這就跟玄幻不是很相似。現在有些科幻小說作者,讓人工智能直接介入他的寫作。讓人工智能先學一遍作家的所有小說,然後再讓這個機器開始根據作家的風格創作,最後把機器和人寫的是結合到一塊。這樣寫出來小說很有意思,而且看不出來誰寫的。現在是用的愈來愈多。
譚劍:自己寫就是最大的樂趣啊?
韓松:他這個人認為機器就相當於他自己。
譚劍:如果大家知道怎麼用AI,請教我,我也挺想試的。
韓松:陳楸帆就在做這個事情。劉慈欣也用機器寫作的,他和譚劍一樣本身也是計算機工程師出身,他認為人的想像力是無法窮盡的,用機器來編造了好多外星世界。我都不知道他把哪個外星世界用在小說裏面。非常奇異,而有的世界造出來,跟我們想像的所有的世界都不一樣。那個世界就是一根直線,但是這個世界是成立的,是真實的。按照機器的邏輯,建立在數學的基礎上,建立在物理的基礎上。科幻小說的很妙的。
劉慈欣當時還創造了一個軟件,他用機器來寫詩,然後他把這個機器寫的詩也跟他的小說結合到一塊。

人工智能會讓科幻作家失業嗎?
譚劍:所以我們要不要擔心人工智能讓我們失業了?
韓松:我們當時跟主流文學的辯論過,我和伊格言還是戰友。
伊格言:我們是站在AI這一邊的。陳楸帆是大陸的科幻小說家,韓松老師也說了,他公司就在做這件事。我剛才就立刻想到一個情節:我發微信給陳楸帆,問他AI可不可以借我。但借不到⋯⋯
韓松:我們都不敢問他。
伊格言:結果有一天我就突然發現其實在微信上面,是他用AI代替自己來敷衍我。
韓松:很厲害,我發現他小說愈寫愈好,每年大陸的星雲獎短篇小說獎都被陳楸帆壟斷了。而且他寫的他用AI寫的小說發表在好多純文學的雜誌上。
伊格言:太可疑了,等下回去真的跟他微信一下,但是他用軟件來敷衍我也不知道。(笑)
譚劍:你要留意的是他給你的那一個版本的軟件,你要最新版,不要舊版的。
韓松:譚劍老師,從創作科幻小說的角度,你覺得有一天AI可以代替我們嗎?
譚劍:其實我一直覺得AI就是去學習你的想法,然後再根據你的想法做出跟你想法一樣的事情。完全能夠做到,因為它設計出來就是做這種事情的。拿古典音樂做比喻,現在有一段貝多芬的音樂,一段電腦做出來的貝多芬的音樂,人類聽到是無法分辨哪個是貝多芬哪個是電腦,因為每個音樂家就是有自己的風格。但我們不是只想聽貝多芬或者巴赫,還希望人類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有潛力的音樂家能創造新的偉大的作品。
在香港我們寫科幻小說是很艱難的,而且我們年輕的一輩甚至包括我也很貪心,我們不止寫科幻,我們也會寫推理,把不同的類型小說的元素全部炒在一起,重新做一樣大家沒見過的東西出來。因為我們覺得這才是創作。
所以在大陸和台灣,你們寫科幻小說是只寫科幻嗎?有沒有碰到其他的層面?

伊格言:我自己是不會遇到這個問題。我一直被視為純文學作家,只是也寫科幻題材,寫科幻題材之後就同時也被視為科幻作家,對我而言這些都是一個可以運用的的元素,只要我覺得有趣或者可以寫的,就把它收集到自己的作品裏面來。我喜歡推理/諜報/神鬼認證,都可以放進小說。
回到AI的話題,我態度比較開放,我認為AI寫的東西作為一個元素其實也是可以吸收到小說裏面來的。基於前面講人類歷史建立在虛構之上這點,我在想,不曉得人類的意識和肉身未來會怎麼變化,人會不會成為真的「人形軟件」?成為一個程式,一個AI?這比較難難以預測。如果人的意識能上傳雲端,程式可以代替人,那麼這套程式如果寫出了小說,這小說是人寫的還是AI寫的?
我想如果這一天真的到來,你就可以跟AI正式交朋友,因為你從人變成一段程式,別人可能本來就是一段程式。接下來,程式與程式之間可以交流對話,最後還可以結婚。只要寫出一道什麼叫做結婚的規則就行。結婚之後你們還可以生小孩,不對,你只要寫出兩段程式如何生出下一段程式的規則來就可以了。這時候,這一段生出來的小程式,它就變成人類跟AI的的混種……
所以我並不是很擔心人類被AI打敗。因為我們最後可能會變成跟AI一樣,我相信大家都會優先選擇通婚,而不是戰爭。讓我們做愛不要作戰。
韓松:我也想提一個問題,結合今天的主題「華語科幻的不同面向」,那麼AI創造出來的作品,是屬於咱們華語科幻,還是一種世界性的科幻?
譚劍:有句話是香港科幻必須放在世界科幻的脈絡下來觀察。香港是個外向型的經濟體,從世界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一直是自由開放的地區,很多出版品可能在其他華人地區出版不到,都可以在香港找到。香港一直很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我的前輩中有從中國大陸出來的,比如倪匡。沒有互聯網的時代,台灣的作者也帶給我很多台灣印象,比如白先勇等。我們都是這樣受不同文化的影響。到後來我們這批人的作品出來又影響後進的人。應該說在這年頭很難有作家不受外地影響。
韓松:理解,香港科幻的面向可能是更加開放包容多元的這麼一個結構。譚劍的小說裏想法的自由流動給我感觸非常的深。那麼。台灣科幻的面向,伊格言老師,能不能歸納一下是什麼?
伊格言:在台灣寫科幻小說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隱隱約約感覺到台灣純文學界,想法比較保守的老師對科幻有歧見。現在資訊流通,一定會看翻譯小說,就像譚劍說的,現代的作家很難不受到其地作家的影響。我們學習前輩小說/翻譯小說裏的冒險的刺激的部分,也希望照顧到純文學裏者塑造複雜的真實人性的部分。
韓松x伊格言x譚劍:華語科幻的不同面向二之二
本系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