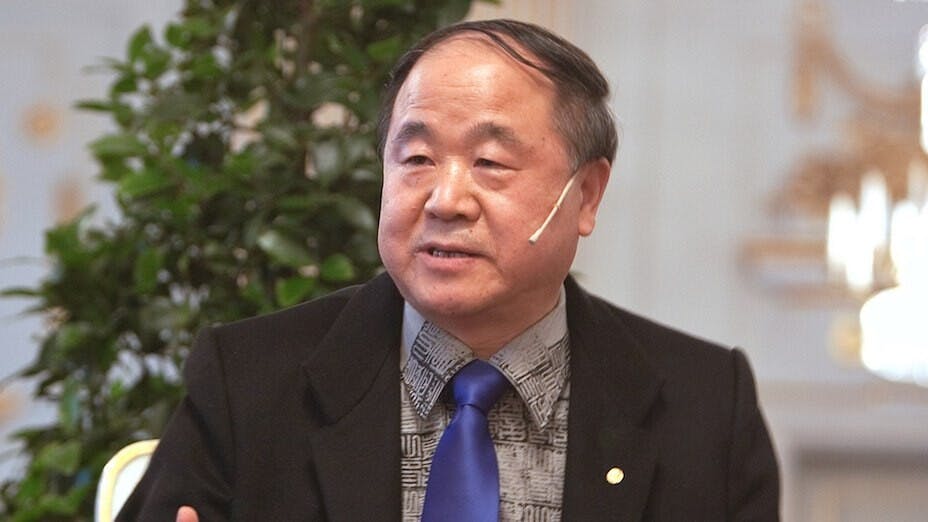現在,我講講閱讀和創作之間的關係,我覺得,創作最好的老師就是閱讀。如果說文學創作或者小說創作有什麼訣竅的話,那就是閱讀──然後就擁有了建立在閱讀基礎上的「魔法」。
閱讀的兩種方法
剛才在休息室裏,一名同學問了我有關讀書的問題。我認為,對年輕人來講,對任何人來講,應該掌握兩種閱讀方法。
一種是精讀,就像我讀我大哥的語文課本一樣,翻來覆去地讀,讀到能夠把其中的主要內容背下來。
另一種是廣泛瀏覽。世界上的讀物浩如煙海,一個人即便是縱有閱讀能力時開始讀,一直讀到白髮蒼蒼,也讀不完其中的百萬分之一,你只能讀非常少的一部分。在這種情況下,把閱讀分成精讀和廣泛瀏覽就非常重要了,你不能總是把一本書很認真地從頭讀到尾。
經典的書要認真地讀,要精讀;對於一般的讀物,尤其是現在網絡上出現的很多東西,一目十行地瀏覽一下,了解一下大概的文風,知道說了什麼,也就可以了。
寫作從模仿開始
有了精讀和廣泛瀏覽的基礎,假如你要從事文學創作的話,就應該從模仿開始。
當然,模仿,對於一個成熟的作家來講,是個不光彩的詞。如果現在還有人問:「莫言,你最近的作品模仿了誰的小說?」我認為這是我的一個巨大恥辱,別人也會對我嗤之以鼻,瞧不起我——都寫了20多年小說了,新作竟然還在模仿別人!我覺得這是一個作家最大的恥辱,說明你沒有什麼創造歷程,你一直在靠模仿生存。
但對於一個初學寫作的人來講,模仿不是恥辱,而是一個捷徑,或者說是一個竅門。我當年在學校裏給大學生講課的時候,也曾經反覆說過,大家不要以為模仿就是見不得人的事情,剛開始寫作時誰都在模仿,包括魯迅,他的早期作品也都有模仿的痕跡,《狂人日記》就是模仿果戈理的同名小說。
魯迅的很多作品,研究者都可以找出模仿的原作來,但這並不妨礙魯迅成為偉大的文學家,因為他很快就超越了模仿的階段,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文風,形成了獨特的魯迅文體。
培養語感最重要的方法
我為什麼要反覆強調剛開始應該模仿,就在於我覺得模仿是培養語感的最重要的方法。我們也經常批評一些作家,說「你這麼大年紀了,怎麼還有一股學生腔調」。「學生腔調」就是指一個人還沒有形成自己的語言風格。
一個人的語言風格實際上跟一個人對語言的感受力密不可分。當年李希貴校長在山東省高密縣第一中學擔任校長的時候,我們討論過這個問題,認為初中階段對培養一個人一生的語感至關重要。如果你在初中階段沒有培養起對語言的感受力,那麼你以後的努力很可能事倍功半。
假如我們在初中階段就掌握了很好的語感,這就像一個從事音樂工作的人掌握了很好的樂感一樣——培養出了懂音樂的耳朵,會為你今後的音樂工作打下最堅實的基礎。假如我們在小學、初中階段就培養出了非常敏銳的語言感受力,那麼它對你將來無論是否從事文字方面的工作,都會非常有用。
培養語感最重要的方法,我覺得就是在反覆閱讀基礎之上的模仿。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我們連續讓學生讀10篇魯迅的著名雜文,然後讓學生寫一篇類似題目的雜文,我們就會發現,幾乎每一個孩子的雜文裏邊都出現了一種魯迅的筆調,出現了一種魯迅的腔調。也就是說,魯迅的文風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每一個學生的寫作風格。

這種模仿實際上是不自覺的,是建立在認真、大量閱讀同一作家的作品基礎之上的。假如我們連續精讀古今中外10位作家的作品,然後有意識地模仿這10位作家,那麼在這個過程中,你自己的東西就會慢慢出來。就像一個有志於學習書法的人,臨摹了顏真卿、王羲之,又臨摹了柳公權,他臨摹了很多碑帖,但他最後寫出的作品與他先前的作品相比,還是有細微的差別。
寫作確實有點類似於書法,你模仿得多了,自己的風格也就慢慢確定了。更準確地說,是你得到了一種語感。得到一種語感對於文學創作非常重要。
如果我要寫一個人內心非常痛苦,這個內心非常痛苦的人走到長安街上,用他的眼睛來看周圍的事物,用他的各種感官──他的嗅覺、他的視覺、他的聽覺來感受長安街。因為他內心痛苦,這個時候他寫出的文字或者說作家寫出的文字,必然帶着一種痛苦、低沉的調子。
反過來,如果這個人是興高采烈的,他還走在這條街道上,因為作家現在想努力表現一個人興高采烈的狀態,他的全部感覺都用在表現這種情緒上。有了這種語言的感覺之後,寫出來的文字自然也就帶上了一種興高采烈的感覺,我想這就是語感。
樂感與語感
音樂也類似。我們當年在農村生活的時候,很多農村的二胡演奏者,他們並不懂簡譜,更不懂五線譜,他們是文盲,一個字都不認識,但是他們照樣可以拿起琴來演奏一首非常婉轉動聽的樂曲。這就是說,他們在長期的模仿過程中使自己的耳朵、手指與樂器之間產生了感覺。
這種感覺我是親身體驗過的。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父親說我什麼本事都沒有,「你看看街上那個瞎子,拉着琴可以去討飯,可以要來很多糧食,我們家掛着一個二胡,你練練吧!」當時我只會拉一些很簡單的革命歌曲,像《東方紅》、《大海航行靠舵手》,剛開始就是閉着眼睛瞎拉。
剛拉兩下,我母親就說:「不要拉了,明天的小米已經夠喝了!」農村有一種石碾,推碾子碾米的時候,碾子會發出吱吱的聲音,所以我母親諷刺我拉二胡的聲音就像推着石碾在轉圈碾米一樣。
「碾小米」大概「碾」了有兩三個月,我就能拉出《東方紅》了。那時,我腦子裏一直想着《東方紅》的旋律,同時手在弦上摸來摸去,摸了兩三個月,我的手和耳朵以及《東方紅》的旋律之間就建立起一種聯繫。也就是說,我的手已經有樂感了。
後來,我聽到什麼曲子,只要記住那個旋律,就可以拉出來了。所以,我就明白我們的民間音樂家為什麼可以一個字不識,根本不懂任何樂曲,也可以拉出他心裏的旋律。
有很多民間的天才音樂家,像阿炳那樣的人,他是個盲人而且是個文盲,為什麼能創作出像《二泉映月》這樣經典的民族音樂?因為他已經超越了模仿別人旋律的階段。他心中巨大的痛苦無法表述,在心裏自然生成了一種悲苦的旋律,表現在他的手和琴弦上,就成了經典樂曲。
我想,文學創作的過程,文學創作過程當中的語言、語感,與音樂家、音樂演奏家們的創作和演奏過程當中的樂感是一個道理,即建立在這種多讀和進行模仿寫作的基礎之上。
我本來想詳細地講一下我的創作,但沒有多少時間了,所以,我只簡單地講一下。我的創作也是分了幾個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我在部隊的時候就開始學習創作了。這個時期主要是模仿,而且模仿得很拙劣。
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開始發表作品,這個階段也還停留在模仿的階段。剛才有同學提到的《春夜雨霏霏》,就是模仿茨威格的《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後來,我還寫過一篇叫《售棉大道》的小說,模仿了阿根廷作家科塔薩爾的作品《南方高速公路》。還有一篇叫《民間音樂》的小說,模仿了美國的一位女作家麥卡勒斯的作品《傷心咖啡館之歌》。
那個階段我還是在模仿,而且很多編輯也一眼就看出來了,問:「這個書是模仿了誰的小說吧?」我說,確實是,但他們還是決定發表,因為這裏邊已經出現了我自己的東西。第一,表現的是中國的內容;第二,語言有自己的特色,有很多高密的鄉言土語,而且融合得很好。當然,模仿的痕跡還是存在的。
走出模仿 邁向文學
我真正走出模仿的階段,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風是在1984年,那是我到解放軍藝術學院進修以後。
我的成名小說應該是《透明的紅蘿蔔》。這部小說所描述的內容跟我個人的經驗有很大的關係。我曾經在一個橋樑工地上為一個鐵匠師傅做過小工,所以我對打鐵的生活非常熟悉。我描寫深更半夜的時候,在秋風蕭瑟的橋洞裏面,一個鐵匠,一個赤着上身只穿一條短褲的孩子,拉着風箱,看着熊熊燃燒的爐火……那種想像,那種很奇妙的感受,都跟我的個人經驗分不開。

那個時候,我的小說不僅內容上中國化了,而且小說所使用的語言也個人化了。所以,我覺得一個作家成熟的最重要的標誌,就是形成了他自己的文風,讓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就像我們讀魯迅的文章,即便把魯迅的名字蓋住,我們依然可以讀出來,這是魯迅的語言風格。張愛玲的小說,也有她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沈從文的小說也有他自己獨特的語言風格。
也就是說,只有當一個作家形成了自己的語言風格,當他的語言為豐富作品做出貢獻的時候,我們才認為他已經超越了一個小說家或者說小說匠的階段,他可以說是一個文學家了。
因此,文學家跟小說家是有區別的,小說家成群結隊,文學家寥寥無幾。所以,在現當代小說家的隊伍當中,能夠稱得上文學家的也就是魯迅、沈從文、張愛玲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人。直到現在,莫言依然是一個小說家,只是一個說書人而已。也許再奮鬥20年,終我這一生也很難上升到文學家這個階段。今後的歲月儘管前途渺茫,但我還要努力奮鬥!
原刊於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