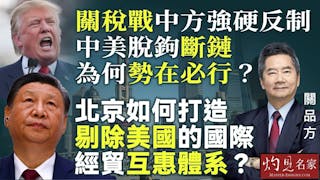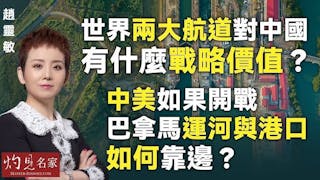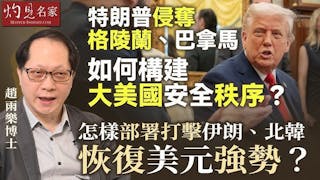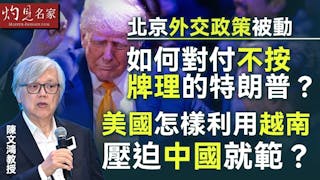中國所面臨的民主問題也是一般民主政治研究中的重要命題,即西方國家的民主體制,是在本國社會政治條件下、在當地政治歷史實踐中所產生的制度性結果,是符合西方文化和實踐的制度形式,還是對世界各國都具有普遍意義?
這裏就引申出幾個相關的重要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西方社會和東方社會,是否具有不同的民主觀?即使在西方,人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也存在很大分歧。亨廷頓代表一種觀點,認為民主的價值觀、模式、內涵只有一種,是西方文化的產物,其他的文化傳統,如儒家和伊斯蘭文化,是不支持民主制度的。
亨廷頓的文化決定論當時受到了很多挑戰,其學生福山(Fukuyama)就不同意這種觀點。福山著文《歷史的終結》,提出西方民主是人類最終的政體形式,不僅具有普世性,且必然擴展到世界各個角落。就東亞民主來說,福山借用了當時美國哈佛大學華裔學者杜維明關於儒家文化研究的個別觀點,認為儒家文化有兩個層面,一個是王權儒家文化,代表的是專制文化傳統,另一個層面是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文化,這部分可以與西方的民主文化相銜接。
福山據此認為,東亞國家20世紀80年代後之所以會走上民主化道路,是因為日常生活中的儒家文化傳統,與西方民主文化傳統接軌了。福山儘管因為此文而名聲大噪,但此後幾乎一直在修正此文的觀點。近年來,有鑑於西方民主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後所面臨的困局,他甚至開始出現批評西方民主的傾向。
2014年9月,福山為其《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再版寫了一篇代序言:「民主依然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儘管他還是基本堅持原來的立場,但其論證仍然從意識形態出發,而非從經驗證據出發。福山的觀點反映了西方學者對民主作為意識形態認同和政治實踐的弊端之間的深刻矛盾。
民主化的促成因素
政治學界許多學者往往將文化因素在民主和民主化中的作用,視為是不可驗證的,因為很難在文化要素和民主政治之間,找到因果關聯。
除文化之外,另一個廣受強調和重視的因素,是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有鑑於西方民主國家社會經濟發達,很多學者試圖找到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民主政治之間的關聯。一般認為,隨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民主往往變得不可避免,因為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往往和教育水平、利益分化、政治參與意識等聯繫在一起,而這些都有助於民主的發生和發展。
不過,這馬上出現很多問題。例如,為什麼在有的亞洲國家特別是新加坡,其發達的社會經濟基礎,卻依然未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體制呢?再者,就民主作為一種制度安排和技術手段(如多黨制和選舉)來說,任何社會,不管其經濟發展水平如何,都是可以民主化的。如果根據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把亞洲社會分成三類,即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社會,就會發現這些社會,有些已經成為成熟的民主社會,有些正處於民主化過程中。
儘管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一,但民主化了的社會都具有西方所定義的民主特徵,即多黨制、選舉、政黨輪流執政等。但不同地方的民主化效果不一樣。人均國民所得1萬美元的國家或人均國民所得2000美元的國家,都可以實現民主化,但兩個民主的品質截然不同,前者通常表現為和平理性,後者則往往表現為暴力和非理性。同時,民主政治又會反過來影響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在亞洲,一些社會在民主化後,政局不穩,導致低度發展;一些社會則在民主化後,陷入了長期的中等收入陷阱;還有一些原來已經達到高收入水平的社會,民主政治無從形成有效政府,從而走向民粹主義,導致經濟發展停滯不前。

由於文化、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民主之間,並不存在對應關係,學者轉而強調領導人對民主的態度的重要性,認為一個國家能否走上民主化道路,最重要的是領導人的態度,民主化進程主要取決於領導人在特定時刻所做的決定。從經驗上說,這的確在一個社會的民主化過程中,起到關鍵作用。
但這又怎樣呢?領導人可以促成社會的民主化,卻沒有能力決定民主的品質。亞洲社會並不缺乏對民主具有虔誠信念的政治人物和理想家,他們終身追求、踐行民主,但並沒能給他們的社會帶來實質性的進步。反之,那些對西方民主抱有懷疑甚至抵制態度的政治人物,反而推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他們生前或者身後常常被那些信仰民主的人們所批評甚至攻擊,但正是他們造就的社會經濟發展,為他們的後人奠定了堅實的民主基礎。歷史有時就是這麼具有諷刺意義。
實際上,對形成今天世界民主格局最具影響力的是地緣政治。西方在推行民主過程中,往往把西式民主包裝成普世的東西,卻把地緣政治這個關鍵要素排擠在視野之外。例如,在「第三波民主化」出現之前,各國政治精英對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和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競賽,有各種各樣的看法;社會主義陣營的制度,在發展中國家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但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蘇聯陣營社會主義國家的制度弊端逐漸顯現,其經濟相對於西方國家日益落後,沒有了競爭能力,同時社會主義制度對發展中國家的魅力也逐漸消失。蘇聯實力不可避免的衰微,也使它不得不結束冷戰,在和西方的地緣政治之爭中落敗。正是冷戰國際格局的終結,促進了民主化浪潮。
亨廷頓所說的「第三波」民主化的發生,有效鼓勵了西方國家。在冷戰結束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再次投入大量的人財物力,把民主擴展到非西方世界。實際上,一些研究民主化的學者,如戴蒙德(Larry Diamond)在上世紀末就預言,第四波民主化即將在中東、北非等專制國家發生。民主化的確在那些國家和地區發生了,但不是內生的,而是西方地緣政治延伸的結果。沒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佔領和其他種種推動民主化的努力,很難想像這些國家和地區會實現民主化。結果又怎樣呢?這些由外力推動的民主,是否符合當地人民的願望呢?
民主化的幾種趨勢
今天,世界又進入了地緣政治大變動的時代。就民主來說,這個時代具有如下幾大傾向或者大趨勢。
第一,儘管西方仍努力向非西方國家推行民主,但也開始反思大眾民主所面臨的嚴峻挑戰。比如,歐洲面臨難以為繼的高福利制度的弊端;美國的民主政治演變成為兩黨互相否決的制度;愈來愈多的社會經濟問題呼籲一個有效政府,但民主政治滿足不了這個需求。同時,由於西方民主國家的內部問題,其外部影響力也開始逐漸衰落,這又反過來影響非西方國家的民主,因為後者往往是西方地緣政治擴張的產物。
第二,隨着西方地緣政治力量的相對衰落,非西方世界抵制西方式民主的力量不可避免會增加。西方力量的衰落意味着外在壓力的減少,讓抵制西方式民主的社會變得更有信心。那些一直仇視西方式民主但又引入了民主制度的社會,主要是中東伊斯蘭世界,更會主動向西方民主進行挑戰,造成當地的無政府狀態。這個過程已經開始,未來如果失敗政府增加,這些地區的形勢會變得更加嚴峻。
第三,一些已經引入西式民主的社會也會開始反思,並且修正西方式民主對本地社會所帶來的困惑。從民主擴展的歷史看,在非西方世界,當民主來到的時候,人們往往給予很高的期待。但是,隨着時間的推移,當人民切身感受到民主不是醫治社會問題的萬能良藥時,他們就會開始反思民主,修正其民主形式。當然,修正民主並不容易。一些社會陷入了「選舉陷阱」,難以自拔;但也有一些地方則能夠通過政治強人,糾正原來制度的缺陷。
第四,還有一些國家和地區開始尋找適合自己的民主形式。這裏,中國佔有重要地位。中國是偉大的文明古國,其政治制度的發展必然要和數千年的文明具有一致性。民主無論是作為意識形態,還是解決政治問題的制度安排,其是否有效運作,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和自己文明的一致性。沒有這種一致性,中國民主也會遭遇亞洲其它許多國家和地區所面臨的困局。
如果說抵制任何形式的民主的發生在政治上並不可行,甚至會導致政治的失敗,不加選擇地引入西方式民主,也會導向同樣的結局。如果說民主不可避免,民主也不可避免是多元的。未來的歷史會告訴人們,贏得最終勝利的,是那些能夠找到符合自己國情的民主模式的社會。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