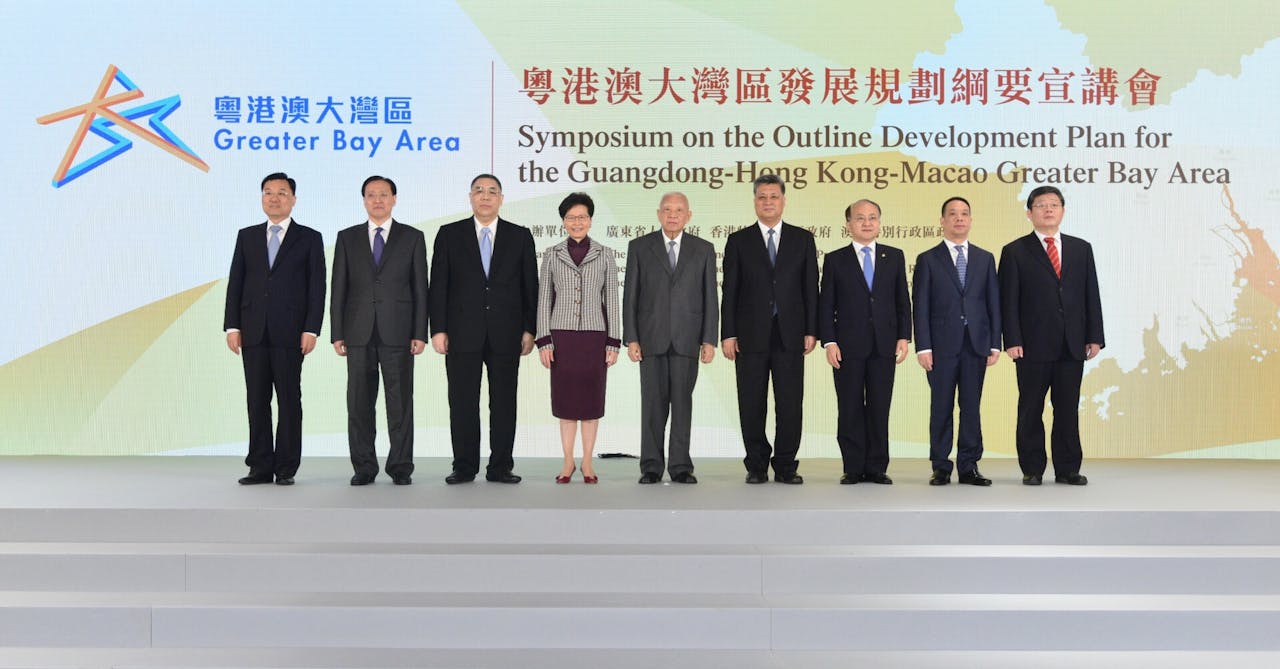剛剛公布的《大灣區規劃綱要》,以及社會的即時反應,都可以是了解國情的好案例,也是理解「一國兩制」的好機會。
香港的許多輿論,即時的反應是:綱領很「虛」。一種解釋,現在只是提出概念,「實」的方案,會逐步提出。筆者是另一種闡釋:中國的許多大的計劃,都是先提出大的方向性概念,大家朝着這個方向「奔」,是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和期望去「奔」。在這個過程中,中央政府會慢慢形成政策,而整個概念,就在這個過程中逐漸成熟。
策略模糊 上下磨合
這來源於幾個經歷。1980年代,開放改革,中央出了不少政策文件。其中最顯著的是1985年的《教育體制改革方案》,把財政權與行政權,下放到鄉(鎮)。隨後有1986年的第一部《義務教育法》,用法律配合義務教育的發展。當年參加了幾個世界銀行的農村項目,就覺得,這類文件都不夠具體,沒有太多的細節。實施的過程,其實是各地在各自摸索。因此,頒布之後,也許很難去具體監控。當時教育部的朋友就說:「文件只是一個大方向,大家就朝着這個方向奔。」這是第一次領略「奔」的意思。
後來在另一個省級政府的諮詢會上,又得到另外一個訊息。教育廳的朋友說:「我們省裏面有自己的發展腳本(劇本)。中央只提出一個方向,下面的省就各自拿出自己的腳本,看看如何可以融合到中央文件的『精神』裏面。」那時候才知道,原來地方政府並非被動地坐等中央的指示,而是要很巧妙地把中央的精神與地方的腳本融為一體。
最徹底的是我的一位日本博士生阿古智子。2003年畢業,現任東京大學教授,成了研究中國的知名專家。她精通英語與中文,花了一年,在上海長時間當教師,設法理解前線學校與教師對課程改革的反應。論文得到很多人的引用。她的觀察,中國的政策頒行,有一種獨特的「策略性模糊」。她的論文題目,就是「Strategic Ambiguity」。也就是上面頒下來的政策,不會太具體,總是有比較寬的空間,讓地方政府可以有足夠的迴旋餘地,因地制宜實施。
在中國執行過項目的世界銀行朋友,聽到這種看法,都拍案叫絕:「對!這就解釋了許多我們覺得不可理解的中國現象。」筆者當年從事公共政策的研究,西方的文獻中,政策的實施(implementation)是一個難點,一般是聚焦實施的結果與預期的目標是否吻合。
這種「種瓜得瓜」的政策實施觀念,在中國有時候就行不通。因為政策本身就有很大的模糊性,也就是只是「方向」、「精神」。
從負面看,這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這說法隱含下面都是在「對着幹」。但是若真是如此,那麼最後的結果一定是政策失敗。令世界銀行的朋友感到困惑的是,好像很多政策,裏面的「方向」、「精神」,又會逐漸實現。他們說「這些年中國的成功,好像也是在這種政策的模糊形態中發生的。」
或緊或鬆 可窄可寬
也可以有「陰謀論」的看法,認為這是讓「上面」易於控制的辦法,也就是說,「上面」可以有很大的空間,隨時隨意制定是非標準。內地的朋友,許多都說,在「政治思想」領域,所謂「禁區」往往難以捉摸,因此誰也不想去碰;但是在一般的發展性的領域,他們卻歡迎這種模糊,因為「那就有了創新與突破的空間」。
其實,這種形態,在中國相當普遍。比如說,高等教育的「雙一流」(一流大學、一流學科)。其實也是沒有明確的定義。只不過教育部遴選出一個名單,各院校知道自己知否屬於「一流大學」,有哪些屬於「一流學科」。大家講的,是「是否進了」,對於「雙一流」是什麼,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因為進與不進,待遇很不一樣」,可見「進入」「雙一流」是一種向前發展的機會。從這個角度看,「雙一流」的政策目標,也就達到了。
又比如「一帶一路」。另外一位博士畢業生,在單位裏面負責「一帶一路」的項目。筆者問哪裏可以看到「一帶一路」原始的、明確的「定義」。她說,只表示一個是陸路、一個是海路,並不明確。有說沿途有47個國家,那只不過是某些研究工作者的計算,中央沒有一個明確的標準。最近還聽到內地的謔話:「除了美國,其他國家遲早都會屬於『一帶一路』。」當然那是說笑而已。
我的另外一位博士畢業生,2006年畢業,研究「民辦教育」(即私立教育)政策在民間的反應。她把中國政策的頒行,分為「緊─鬆」與「明確—模糊」兩個維度。有關「意識形態」的(目前主要是「黨的領導」),會「緊而明確」。
除此之外,在民辦教育的領域,則似乎是「鬆」或「模糊」,因此民辦學校品種很多。近幾年,各式各類的民間集團辦學,數不勝數,打破了筆者數年前「中國缺少另類學校」的論斷。近幾年,也興起國際學校的浪潮,那政策可以說是「既緊且鬆」:緊,必須有中方辦學夥伴,必須有黨委;鬆,在招生、課程、電子網絡,可以有種種的灰色地帶。
各有腳本 最忌坐等
在內地生活和工作,很習慣如何不去碰「緊」的區域,按照「明確」的規定辦事,但是在「鬆」的「模糊」的領域,則盡量探索和擴大空間,謀求多元、創新、脫俗與突破。教育如此,其他的領域更是如此。
在香港人沒有這樣的頭腦,也不需要這樣的思考。但是在媒體上流傳的,大都是純粹用政治觀點看中國的任何政策。處於恐懼,就往「緊」的與「明確」的方面鑽。於是把原來是「鬆」,以為背後一定有「陰謀」;又把本來應該慶幸的「模糊」地帶,要求「明確」,其實是在縮窄自己的天地。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如何,每個地方必須有自己的「腳本」。有自己的腳本,才能在大環境的變化裏面,找到自己發展的方向、出路與優勢。也就是說,即使在內地,中央是不會代替地方編寫這腳本的。看看現實,坐等中央指示的省份,一定是一蹶不振。
問題是:香港有自己的腳本嗎?說得不客氣一點,我們佔據着立法會議席的各個黨派:在電視機面前看來理直氣壯,甚或殺氣騰騰,心中可有香港發展的藍圖?很多事情也許都值得反對,然而,反對之餘,可有想到需要推動什麼?香港的發展應該有什麼前景?尋找什麼出路?利用什麼契機?營造什麼環境?期待什麼優勢?周圍的大環境,不管是中國還是世界,不管是順境還是逆境,香港都需要向前發展,需要有願景,需要推動。
另一點值得注意的,中央政策的模糊,也表示:中央計劃外的,不等於不能發展。例如教育。《大灣區規劃綱要》,從文字看,香港主要是發展金融經濟等的國際地位;然而,看不出大灣區發展的綱要,會對任何其他的發展造成障礙。
教育為例,文化與教育的發展中心不在香港。這也不難理解,在內地尤其是專門從事意識形態的看來,香港的教育是「重災區」。但是香港的教育,在國際上享有盛譽,那也是不爭的事實。香港的教育,也絕不會因為大灣區的發展而停下來。假如相信馬克思──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假如香港經濟出現新的景象,香港的教育與文化也必定會出現新的飛躍。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