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言路阻塞的社會,人們難以直言批評體制弊端,往往「彎(繞)道表達」:藉歷史故事、幾百年前文學作品的情節和對話,影射社會現實或迂迴進諫。
這就是理性表達的「移情投影」。人們不停留於對歷史的回顧、對文學作品的欣賞,而是在回顧、欣賞中「昇華」:移情於社會現實,帶出諷刺或期待之情。
德國劇團在北京公演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寫於1882年的《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在南京被逼停演,引起了轟動效應,其因關乎觀眾的「移情投影」。
演人民公敵 南京遇障礙
挪威的劇作家易卜生,早在1920年代就為中國讀者熟悉。三幕劇《玩偶之家》(1879, 又譯《娜拉》),很早就在上海等地演出。香港喜愛芭蕾舞劇的人,可能更熟悉五幕詩劇《培爾.金特》(1867,有蕭乾譯本),這或與改編為芭蕾舞後的插曲〈清晨〉和〈索里維格之歌〉(註1)的優美旋律有關。
9月上旬,柏林邵賓納劇團在北京的大劇院演出五幕劇《人民公敵》。劇本收入人民文學出版(北京)的《易卜生戲劇集》(2006)第2卷,譯者潘家洵是易卜生專家。譯文中的術語,略帶紅色中國(紅中)特色,例如把歐洲小城的地方官吏稱為地方領導人、咱們的領導人(卷2,頁240、244)。
《人民公敵》在北京公演引發的「移情投影」,使宣傳官(審查官)警惕,封殺了原定9月中旬在南京的演出。演出原是德國歌德學院與南京大學文學院的合作安排,因劇團拒絕修改劇本的一些對話(所謂敏感話題)而停演。官方有「包裝性說法」:「因舞台技術原因」而停演。
政局續左轉 政審更苛嚴
胡溫新政時(2003年3月至2013年3月),《人民公敵》曾在紅中演出;北京的人民藝術劇院也曾演出(香港於2017年以廣府話演出,由鍾景輝和萬梓良「讀劇」、馮祿德導演)。
胡溫新政時,有些歌手的歌曲也受限制。2011年,鮑勃‧迪倫在壓力下「自我約束」,不唱招牌曲〈答案在風中飄蕩〉(Blowing in The Wind),其歌詞有「一個民族生存多久才能獲取自由」之問?
2013年3月後,政局左轉衍生亞文革(註2),文藝的政治審查趨緊。德國著名的德累斯頓十字童聲合唱團,在紅中巡迴演出,向審查官妥協停唱〈思想是自由的〉。德國文化界抗議不能演唱此曲,稱合唱團向專權者「下跪」。
這次邵賓納劇團沒有「下跪」,但在北京第二天的演出,取消了互動安排。紐約時報的署名評論〈易卜生話劇《人民公敵》在中國遭審查〉(Ibsen Play Is Canceled in China After Audience Criticizes Government),聲稱北京當局增強「文化的審查和控制」,並「已達到新的極點」。面對政治審查,是「下跪」還是「打退堂鼓」,是外國藝術團無可迴避的選項。
戲劇揭謊言 觀眾有聯想
《人民公敵》的故事,發生於挪威沿海的小城。主角、公共溫泉浴場的醫生斯多克芒,發現浴場被污染、影響市民健康,提出重建浴場的建議。污染源是本地一家皮革廠排出的污水,他的建議受到與此有關的利益集團阻撓。後來,市長、皮革廠老闆和《人民先鋒報》編輯等串通,藉市民大會裁定醫生是「人民公敵」,並解除其浴場的醫務公職。
劇本透過描寫醫生的自由觀、環保觀和獨立思考,帶出「多數人專政」的話題:有權勢的「多數派」,藉人民之名壓制說真話、站在真理一邊的少數派。醫生揭發強勢一派的謊言,他說:「《人民先鋒報》真荒謬,天天在報上瞎嚷」,「想把本地的繁榮建築在撒謊欺騙的泥坑裏」(卷2,頁250)。
在亞文革的政治生態下,《人民公敵》在北京公演有更強的「聯想現實」誘因。環境污染(涉及官商合謀、捏造環保數字)、官商勾結、官場貪腐、官媒說謊、愚民宣傳,是常見的現實場景。給環保、維權者加上「尋釁滋事」、「煽動顛覆政權」罪(類似「人民公敵」),亦司空見慣。有思考力的觀眾觀賞戲劇情節時,對現實的聯想多而衍生「移情投影」。
在毛時代(1949—1976),編造「人民公敵」罪名整人,就是平常事。曾任社會科學院院長、政協副主席的胡繩(1918—2000),在一篇文章中提過這樣的「荒謬」:
「有些人因為肯於想問題,敢於講真話,一下就成了右派,成了『人民公敵』;有些人不想也不說,或者說假話,就沒事了。」
了解這段歷史的年長觀眾,在觀賞《人民公敵》中有聯想現實之情,亦十分自然。
《人民公敵》在公演時,透過字幕和英文翻譯而有「演員與觀眾互動」,由演者提出話題讓觀眾回應。觀眾的回應是:「他(醫生)是正直的人」,「我們也受污染」,「我們的媒體也不講真話」,「我們要自由」(大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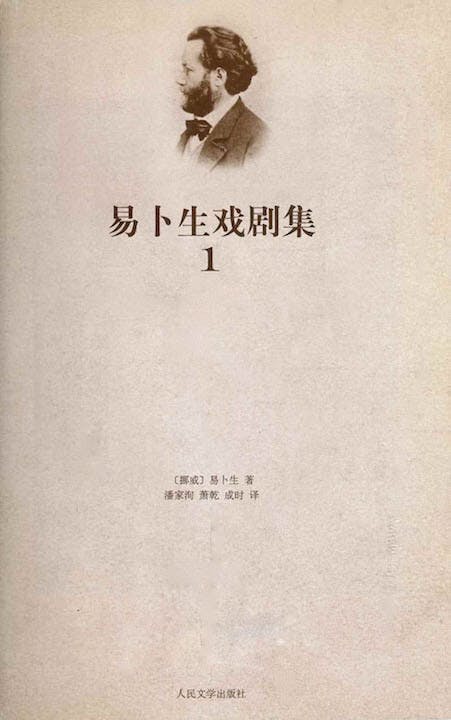
話劇與現實 非常之巧合
《人民公敵》引起的關注,主要在社會現實的「聯想性」,網絡平台的留言,大都提到劇中情節的「現實影子」。
《人民公敵》與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1984》,對紅中的政治現實具有「預言性」,是「非常」的巧合。
《1984》是政治諷刺小說,描寫蘇聯東歐政體下社會的恐怖、人的恐懼。其「預言性」,在於監控器材的「先進化」;讓人們聯想到,紅中現在的大數據(雲端技術)監控、人臉識別器的廣泛使用,「證實」了《1984》的預言。
136年前創作的《人民公敵》,不是、也不可能預言當今的紅中,但它觸及的自由、環保、媒體、權力話題,則與紅中常見的社會現象「巧合」,「巧」得幾乎可以「對號入座」。
這種「巧合」令人在聯想現實中有「預言感」,並在「演員與觀眾互動」中,說出自己的聯想,對特權、腐敗、社會不公、弱勢群體受壓制的不滿。
以反諷手法 為公義吶喊
《人民公敵》的更深層意義,是易卜生的反諷,這是上述回應者未想到或提到的。
劇中的醫生,說出環境污染真相、提出整治排毒的可行方案,但在官商權貴勢力和靠近官方媒體的壓迫之下,淪為被驅趕的「人民公敵」,這是對公平、正義的反諷,也表達對權貴勢力的「無力感」。這或是引起北京思考型觀眾共鳴的一個原因。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