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數十年來,曾有過數次保衛釣魚台島社會運動的出現。在上世記七十年代初出現了第一次的保釣運動。第一次的保釣運動無疑是以大學生為主體的。當時入讀大學不久的我,也就無可避免地捲入了歷史洪流當中了。有關釣魚台島的歷史相信已是眾所周知的事。釣魚台雖然在中國明朝的古籍已有記載,但只是無人居住的荒島。在清日甲午戰爭前已遭日本佔據,《馬關條約》將台灣及其周圍的島嶼割與日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戰敗遭美國接管;在1971年,美國將琉球歸還日本,並將釣魚台包括在內;自始之後,日本即實質控制之,直至現今,中共也無意奪回,雖然中國的軍艦偶有在其附近浮游戈。
反殖民地主義的保釣運動
七十年代初的保衛釣魚台的運動,無疑是受到民族主義的挑動;但是,回望起來,當時首次發起運動的留美華人學生,其實是針對中華民國政府的,並非中國大陸。當時留美學生絕大多數是台灣學生,據資料,約有2萬多名,而香港學生也有千多名;台灣前總統馬英九也是積極的保釣分子。留美學生藉着保釣運動而找尋國家認同;而在台灣專制政權的影響下,這又是一個社會抗議運動。台港留美學生在1971年1月29日第一次示威。
之後,保釣運動傳到香港,香港有「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之成立,主要是在職青年人,並在1971年2月18日在日本駐港領事館前舉行第一次示威,人數約20人左右;緊接着的是2月20日的再次示威。第二次示威由《70年代雙周刊》發起的。這次行動的參加者中已有本地就學的大學生參與。筆者當時也參與了這次示威,記得當時只有20至30人,沿着中環的電車路向着德忌笠街的日本文化館前進時,港英警察沿途重重監視。當時的公安條例嚴苛,4人聚會即可被控非法集會。在日本文化館聚集時,人數大約有40至50人。
在日本文化館前,當時的著名文化人胡菊人先生就站在我的旁邊。後來的4月10日,4月17日在馬料水中大祟基書院內的示威,以及7月7日的維園大示威,筆者都有參加。在4月10日的示威當中,警方已開始拘捕示威者,共拘捕21人,其中7名是大學生;而在7月7日,當時的警司威利更將學生打得頭破血流;之後,在1972年的5月13日,亦是保釣示威的最後一次,自此運動就轉入了另一個形式,保釣運動在香港的興起,與其說主導是民族主義,不如說是反殖民地主義。
1971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取代了中華民國而成為中國唯一合法代表。1972年的農曆新年,美國總統尼克遜歷史性的訪華,中美雙方均走出了開創性的一步。主流的學生思潮轉向了中共政權的認同,興起了所謂「認祖關社」的運動,這已是後話。事實上,保釣的最初參與者,對中共並無幻想,參加的只是對殖民地不公義的抗議而已。之後的「盲人事件」,「六.一八雨災」事件,以至於「反貪污、捉葛柏」事件就是反殖民主義的延績。
第一次參與公開示威遊行
我記得首次參與保釣運動示威是在1971年2月20日的那次。這個日子我記得特別清楚,正是因為是我第一次參與公開示威遊行。兩日前,即是2月18日,一班社會青年組織了「香港保衛釣魚台委員會」,舉行了第一次示威。我現在認識的及仍在交往的朋友中,有兩位周魯逸(筆名魯凡之)及吳兆華參加了當日示威;其中周魯逸仍津津樂道當年的保釣運動。
我所參加的示威遊行是由《七零年代》雙周刊發動的,這份雜誌值得一談。這份雜誌由莫昭如(現在香港專注於藝術戲劇創作)和吳仲賢(已故) 所創刊。一創刊,就打出反殖反建制的旗幟,在六十年代末的白色及紅色恐怖中震開了政治悶局,大大地刺激了青年學生的政治觸覺。我在中學時代就開始寫文章,後來在主編中學的學生報中,寫了一篇反美國參與越戰的文章,不足1,000字,是以書信的形式刊出。《七零年代》雙周刊出版的第一期,就轉載了我反越戰的文章。同期,他們也轉載了中學高我一班的同學任威霖(已故)的一篇英文文章,介紹及論述英國著名哲學家波柏爾(Karl Popper)的學術論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兩位中學生的文章,為外界社會公開發行的刊物所轉載,恐怕是十分罕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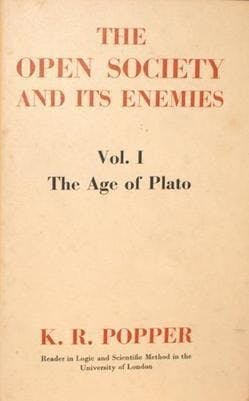
參加同日示威的,還有我的大學新亞書院的同學周鍚輝及顏國明。周鍚輝當時是新亞學生會會長,而我和顏國明是幹事會成員,我是出版幹事。那次示威的起點大概是天星碼頭或者大會堂低座和皇后碼頭中間的廣場,以後多次的示威都是從那裏出發的。
示威的終點是日本文化館,當時的日本文化館是在現時的德忌笠街中段。我們的人數約有20、30人左右。在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政府立了嚴厲條例控制人群集會,多過4人而不經批准即可以被檢控。我們有一條紅色的横額,寫着「保衛釣魚台」,另外有其他的口號,如「反對美日勾結」,「同胞們,行動吧!」,「抗議美國包庇日本!」等。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和顏國明以及另一些青年朋友握着大横額,站在前列,沿着電車路軌上排列,向前方走,旁邊站滿了警察,指揮者是一位英國人幫辦,虎視眈眈,旁觀者不多,當日並不是假期。在日本文化館前,我們層層圍着大厦的出入口,同時高叫口號。當時站在我旁邊的是著名文化文人胡菊人。胡先生現在加拿大定居,後來他娶了我的大學同班同學劉美美;結婚之日,我現在的太太是她的四位伴娘之一。當時著名學者牟宗三及徐復觀也參加了她的婚禮。
胡先生曾主編《中國學生周報》,他在《星島日報》寫的專欄《坐井集》影響深遠,被稱為青年導師。示威之前,我們已經認識,我在中四的時候,在中學組織的時事學會已經邀請他回校主講哲學思潮存在主義。當時在示威隊伍中,我們並没有交談,只是互相凝視。他當時是著名作家,而我僅是一個大一的學生,對他不敢攀談。
整個示威歷時大概個多小時,示威之後也就平靜散去。但在下次4月10日的示威,港英警察即大舉捕人了。我在首次示威後,心情頗為複雜;對警察,我卻不大有恐懼,不過細視自己之性格,卻不是行動型。自己的長處是在思考及理論學習,所以自己也不大想參加以後的示威了。
《七零年代》扮演保釣先鋒
在保釣的示威浪潮中,《七零年代》的確扮演了先鋒的角色。吳仲賢及莫昭如兩人是有魅力的青年領袖;在他們領導下,《七零年代》發動了2月20日示威、五四示威、五一六示威以及六一三示威等,其中4月10日,有多名大學生參與的示威當中,警方開始捕人。
4月10日的示威,我忘記了大部分的細節,只記得在現今的皇后大道中及德忌笠街附近(示威的終點仍然是日本文化館),警方追捕年輕人的走避情況,也記得莫昭如站在愛丁堡廣場(現滙豐總行對面)花槽邊的高處呼籲示威者儘速离開的場面;後來知道中文大學有7名學生被拘捕,其中有我認識的崇基地理系學生廖淦標(現在美國)。
在這次保釣示威運動中,大學生的反應的確較遲緩,由大學學生會組成的「學聯會」,在4月16日才組織一次校內的示威活動,這次示威我有參加。示威是在馬料水崇基學院舉行的。當時新亞書院及聯合書院還未搬入馬料水,相信參加者絕大多數是崇基學生,我估計大約有200至300人左右。由於是在大學內示威,較為保守的學生是願意參加的。活動主要是由學生會的頭頭帶領,喊了一些口號,帶着橫額,繞着崇基的運動場走一圈,相信是大約歷時一小時左右。同日,港大校內也有示威活動。
流血告終的七七示威
學聯組織的首次公開示威,則是在7月7日的維多利亞公園。那次示威,我在現場,但並非是示威者,而是準備採訪替《新亞學生報》及《中大學生報》寫稿。記得我在新亞學生會中擔任出版幹事,自動成為《新亞學生報》的總編輯;同時亦要擔任《中大學生報》的編輯。中大編輯決定做一個有關七七示威的專輯,派我去採訪。
當日的維園,一開始氣氛十分緊張。以園亭為中心,前面的草地坐着數以百計的學生,其周圍則是警察。我是負責採訪的,並沒有坐下來。我提着小型的錄音機,在一個足球場附近蹓蹥,看看可以訪問什麼人。在一個硬地足球場上,看到一個短髪穿白色短袖裇衫及灰長褲的中年男子,截着他問他一些有關保釣感想;但是後來他愈講愈激昂,甚至大聲呼叫起來,這時圍着我們的人們愈來愈多,那個男子甚至叫起口號來,群情有些洶湧了。我遠望草地那邊,警察已經開始捕人,驅趕人群了;不久,那個白衫中年男子就被警察帶走了。18年後的一天,全世界的注視力都釘在北京,大鎮壓已開始了。然而,電視機畫面上,地點是瀋陽,一位記者正在訪問一位短髪穿白色短袖裇衫及灰長褲的中年男子,問他昨晚在北京所發生的事,他愈講愈激昂,甚至大聲呼叫起來,不久,那個白衫中年男子就被警察帶走了,保釣運動的記憶,一下子全回來了。
那一天,另一個深刻印象是在人群驚慌之中,我碰見當時的中大同系同學劉美美。她也在維園內,記得只對她說了一句:「你為什麼在這裏;快些離開吧!」,後來就失去了她的踨影。劉美美後來嫁給著名文化人胡菊人,而我現在的太太當年是四個伴娘之一。她後來定居加拿大温哥華。
在草地上,大批同學盤坐在一起,警察如狼似虎地衝入去,見人就用警棍打,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就是威利警司,很多人被他打得頭破血流。但是,我亦看見他從背部給一位青年踼到整個人向前衝了七、八步才停止,當時港府出動了數以百計的警察。
保釣運動至七•七維園示威而至高峰,也是唯一的一次演變成流血事件。至1972年5月13日的學聯組織的一次向日本領事館的示威,已是尾聲了。隨着美國將琉球還給日本,而兩岸政府也並無行動,這一波的保釣也就慢慢消逝了,但是多年後,釣魚台的主權問題卻未曾消失。自此,我再地沒有參加過保釣運動的示威活動。回想起來,香港保釣運動的思潮實可分為兩股:左冀的社會主義思潮,包括後來的托洛斯基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右翼的是民族主義。後來民族主義導致大專界的「認中關社」的運動,全面認同中共的毛式社會主義,而終於在「四人幫」被拘捕後,這種認同完全崩潰。數十年來,歷史弔詭地發展,中共利用黨國資本主義達到了「強兵」的目的,令到民族主義復甦;而社會主義者大多已成功轉型,成為建制的改革者或合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