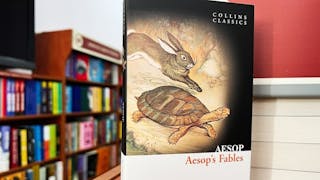歐洲的復興、啟蒙、現代化
伊比利亞即日後的西葡二牙,當時被回教摩爾人(Moors)統治近800年(711-1492),它的重鎮哥多芭(Cordoba)、塞維利亞(Seville)和杜麗多(Toledo)等,與回教帝國的大馬士革(Damascus)、巴格達(Baghdad)和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等,全都設有高等學院(madrasa),形成回教勢力範圍內一個傳授和研究學術的大網絡。這些學院保存有古希臘和羅馬的典藉(希臘文和阿拉伯文),而各地的學者(當中有阿拉伯、波斯和猶太人,甚至是基督徒)均可在這網絡中自由往來互訪交流,除神學外,亦有延續發展古希臘和羅馬的學問,尤其是在哲學和科學方面,前者如亞里斯多德學說,後者如天文學、數學、光學、醫學(特別是眼科)等等。在中古後期,這個回教網絡的科技水平實已超越中國,成為全球之冠,更成為歐洲人的學習對象。
與此同時,歐洲亦開展了它的興辦大學運動,由1088年的博濃娜大學(University of Bologna,在北意大利)起至1400年間,全歐便陸續建有約60所有現代意義的大學,所有這些學府都是有王室和教廷支持的,而王室主導索古翻譯和研習,早由法王查理曼(Charlemagne,742-814)已開始。這個大學運動的近因,是古羅馬法典(Corpus Juris Civilis,由拜占庭的查士丁尼大帝在529年編訂)的重新發現,約在1070年起在博濃娜被傳授,所以初時的歐洲大學,是以法學、神學和哲學研習為主的。而這個法典的重新被應用,亦牽涉到當時的一次宗教改革(Gregorian Reforms,1050-1080),即是由教宗額我略七世(Pope Gregory VII)發起的改革,是教權與王權在歐洲長期拔河賽中,教權一次關鍵性的勝利。

歐洲的文藝復興,便是在上述的大環境下,在法學、神學/哲學、科學、文學、藝術等領域的先後復興。而在這時期中,亦有長達近200年的「十字軍東征」(1095──約1272)和蒙古軍進犯(1240年代)同時發生,這有助歐洲人在商業和軍事、包括航海和熱兵器技術方面的發展,且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一大契機。已故學者黃仁宇的精闢學說之一,指出「用數目字管理」乃現代化的重要指標,而阿拉伯數字(實源自印度)在1000年左右便進入歐洲,複式簿記約在1300年開始在意大利使用,到了哥倫布訪美洲時已成歐洲的會計標準。同樣重要的是,阿拉伯數字是現代數學/科技的必須工具,很難想像今天仍用古羅馬或古中國數字去做數學演算和分析。
啟蒙運動,是繼文藝復興後,歐洲人對科學和文藝等領域的再次提升,但這個經康德闡釋的啟蒙,與之前的復興有一重大區別。此際歐人已不滿足於現狀,是次變革遂有一定的顛覆性、要破舊立新,如馬丁路德的宗教革命(Reformation)和相對的反宗革(Counter-Reformation)、哲學的理性主義、霍布斯/洛克/盧梭的政治理論、亞當史密夫的經濟理論、文學的白話/寫實/人文主義深化、古典音樂的發展、天文學的太陽中心說、多項科學定律的發現、蒸汽機的發明、工農業的機械化和工廠化、等等,屏棄了羅馬教廷堅持(即被貶為蒙眛)的地球中心說、經院哲學、吃人的禮教、拉丁文、聲樂音樂等的禁忌。緊隨着啟蒙運動,歐洲便進入了澎湃的工商業、政治革命大時代。
歐洲的復興和啟蒙,二者皆有一個重要的前提,便是之前的所謂「黑暗時代」(即中古的前半期,500─1000,西羅馬帝國覆亡後的混亂期)。此500年乃歐洲科技和文藝發展的一大斷層,主因是戰亂,次因是基督教會(不是宗教信仰本身)的威權性。教權在英法等大國中,可算與王權勢均力敵,但在各城邦小國中(佔西歐大半),教權便常凌駕於個別君權之上。故此,任何的文藝和科技發展,必須符合羅馬教廷的準則,一經被定罪為異端邪說,是可以被判處極刑的,遲至啟蒙時期,伽利略(Galileo,1564-1642)的屈膝便是極佳例子。
針對這黑暗,歐洲才有復興和啟蒙。但這樣的黑暗時代在中國是沒有的,儒家思想也好,其他重要諸子思想也好,中國不曾有此長達500年的斷層。百年的元朝,或許有「九儒十丐」之說,但到了元中葉(元仁宗任內),以儒學為主導的科舉取士制度又再恢復,一直維持到清末(1905年)才被取消。
另一個大分別,便是歐洲有一個堅實的科學傳統,就算在黑暗時代,這傳統仍由部分歐洲(如伊比利亞半島、東歐)和周邊的回教地區傳承着。在復興和啟蒙時期,科學家普遍上是受到尊重的(在中國便會被指責為「奇技淫巧」,縱有李約瑟的大作指出古中國之科技實高過歐洲,但不普及、實只是極少數菁英的「武林絕技」),而新發展的工業、科技、和日新月異的日常用品如肥皂、牙膏、眼鏡、手錶、攝影、紙張、等等,皆與歐洲人的生活息息相關,再加上有如百科全書一類的普及性讀物,故此連一般人對科技都有一個基本認識。
但在五四時期的中國,差不多所有有能力參予公共討論的菁英,都是科技的門外漢(孫文、魯迅和丁文江等是極少數例外),科技絕少是他們的大專本科或專業,就算是,這些少數人充其量亦只算是新丁,他們對科技的認知,可說是「膚淺、貧乏、混亂」的(周策縱語),知識菁英尚且如此,一般民智便可想而知。當時一個所謂「科玄論戰」,便展示出這些菁英(論戰雙方)對科學/科技、文化/文明的膚淺和混淆認知。
中國的啟蒙、復興、現代化
五四是復興和啟蒙的超濃縮中國版,歐洲人用了前後800多年,中國至今才100年,雖有先例可緩(美國和日本的現代化便是),但相信中國的復興和啟蒙,仍有一段長路要走。中國的復/啟次序,剛好與歐洲倒轉,五四是啟蒙在先、復興在後。
五四提倡白話文,它是文言文的顛覆(正如歐洲的拉丁文被取締),而打倒孔家店便是個更大的顛覆(如尼采的《上帝之死》),是一種推倒重來的啟蒙,在五四之前的新文化運動便已開始。當時中國的啟蒙推動者,一來可能厭倦「中體西用」拖泥帶水式的改革、而甲午戰敗便是一大醒覺,二來可能見到日本明治維新「即食麵」式的成功例子,便偏激地推出啟蒙、全盤西化、「科學萬能」等口號。
而五四後期的復興者,實是部分人對過分顛覆的顛覆:如提倡新詩的胡適,後來多鍾情於古體詩,更樂於整理國故(但仍是用科學方法);不少五四文人如梁啟超、魯迅、林語堂、柳詒徵、張君勱、錢穆、錢鍾書等等,他們的寫作實含頗多文言成分,詩作更多用古體(魯迅的70餘首詩作中只有6首是白話);毛澤東的傳世詩詞,不用說全皆古體;而曾經猛力批孔的人民共和國,現時又正在全球大量興辦孔子學院了。至於有說清代的乾嘉和訓詁學,便是中國文藝復興的濫觴,此仍似是而非、極牽強之說。
毫無疑問,啟蒙與復興亦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取向,啟蒙者傾左、復興者傾右。啟蒙的激進者視復興為保守、反動,更將五四升級為政治運動,把西方的社會進化論、馬克思/共產主義引入,陳獨秀便是中國共產黨的首任總書記。而這邊廂的復興激進者,便將五四推向國粹和復古的方向,把華文化帶去訓詁、國故、新舊儒家的幽徑中,更吶喊出「科學破產」的口號。1960年代,針對國內的「文化大革命」,台灣便推出「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那麼「科學與民主」呢?五四精神至今尚有無餘熱?有無用?若從宏觀的中國現代化去考量,當然有,對科技、文藝、民主的未來提升,更可能是極重要的能量。中國的現代化,正如溫總理所言,尚有一段漫漫長路,鄧小平講的讓一些人先富起來已做到了,但遊客只須行遠半步,到大都市主要通道旁邊的內街坊里、或到農村去看看,國內的人均GDP現實便一覽無遺,不少地區的民智仍待開發。同志尚須努力、現代化尚未成功!
相對台灣而言,中國內地一直都是五四擁躉,馬共主義者更自視為五四啟蒙的承繼人,改稱五四運動為「五四文化運動」、「新啟蒙運動」,並將5月4日訂為「中國青年節」,對岸的台灣則訂為「文藝節」(在國府遷台前的1944年已訂)。無論是青年節也好、文藝節也好、文藝青年節也好,但望兩岸三地對五四的熱忱能延續下去,確確實實地把五四精神納入華文化的一部分,將五四推廣為全球華人一致共慶的日子,便功德無量。
中國的現代化和真正的五四精神,應該是啟蒙復興並用的,一些落後的物質文明東西,便應除舊迎新,自創或直接引進外國的科技和經驗,而某些非物質的文化東西,應以復興的態度去保育或更新,如儒家思想中的「個人修身哲學」部分。崇洋、西化等詞彙,在這一人一智能手機、資訊以光速傳播的時代已極度過時,這是一個全人類互相學習的新紀元,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出現的新事物,其訊息很快便會傳遞到另一角落,有用的便會有人跟進研究,正如鄧公的實用主義名言:「不管白貓黑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本系列文章:五四運動與中國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