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粵語有「定性」一詞,義為「能集中精神做事」。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釋為「耐性」,似不夠準確。

嗚呼是我們日常表示「失敗」、「完蛋」等意思的詞。劉扳盛《廣州話普通話詞典》收錄此詞條為:「喎呵」,條云︰「歎詞。完蛋了。」

「乎」在古代常用做表示疑問的語氣助詞,如《戰國策‧楚策(四)》中︰「中射之士問曰︰『可食乎?』」,即為粵語「可以食㗎?」。詳見「乎」的讀音與用法演變詳解。

粵詞當中有不少嘆詞,靈活生動地反應說話者的感受。原來這些嘆詞也經歷了許多個世代,傳播至今!

粵語形容人忘恩負義,有「反骨」一詞(如「反骨仔」就是「忘恩負義的人」的意思)。筆者一直懷疑這與「相學」有關,其後到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網站查找古代文獻中有否「反骨」的用例,終於找到了以下資料。

粵語表「有錢」一義時,有幾個說法,其中一個是「有銀」。如「你成日叫我買樓,我邊道有銀啫?」就是「你整天嚷着要我買房子,我哪裏有錢?」。

粵語「屎」用作「燒剩下的渣」是古已有之的,而閩南話同樣傳承了這個古語詞。

「坐定粒六」源於賭博術語。擲色子最大之數是六,肯定得六點,即一定得勝。

古代漢語和粵語一樣,「揚」作「宣揚」解時,是可以自由運用的。

若我們口頭上的「唔多」是古語之遺的話,古代文獻當有寫作「不多」,而義為「不大」的表達方式。

晉 葛洪《抱朴子.博喻》已有云:「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這是勸那些身居高位者,用人時要注意用人的長處,不要偏愛「gɐt2」(責難)人的短處。

我們實在不當妄自菲薄,視自己的母語為非雅語,進而拚命拿普通話詞彙來取代自己的母語詞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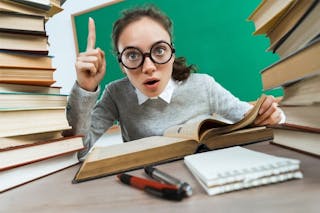
孔夫子有教無類,來者不拒,所以他的學生什麼人都有;無怪乎當時人也有認為孔門很「雜」。

近日筆者在一些電視劇集裏面不止一次聽見藝員的對白看到「初來報道」四字。筆者真的覺得很奇怪。

說到「十」這個字的寫法時,粵語會說是「一劃一㢥」,也就是「一橫一豎」。

粵語「得意」是「可愛」、「有趣」的意思。其實「得意」當是「得人意」的省略。「得人意」即「合人心意」,「得人喜愛」的意思。

「揭」有2000多年的歷史,「屙」和「定」都有過千年的歷史。粵語之雅,於此可見一斑。我們對自己的母語有多大的誤會,於此亦可見一斑!

筆者小時又聽過某廣告,裏面有「痕癢」一詞,於是一直以為粵語的義為「癢」的「痕」,若要在語體文中表達,就可以用「痕癢」這個詞。到了執教鞭之後才知道原來現代漢語共同語當中根本沒有「痕癢」一詞。

「不要碰我的東西!」這個詞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作「玷」。其實「玷」只有「污點」和「玷污」的意思,重點在「污」,而非「觸碰」。

在粵語裏,「個」這個量詞,有一些比較特別用法,其中一個是︰可以用於定語和名詞之間,表示領屬。如「我個頭」就是「我的頭」。

「同化,指兩個本來沒有意義關聯的詞,由於經常處於同一語言結構中,其中一詞受另一詞意義的影響,由於類化的作用,也產生了與另一詞相同或相近的意義。有人把它叫做『沾染』、『滲透』或『同步引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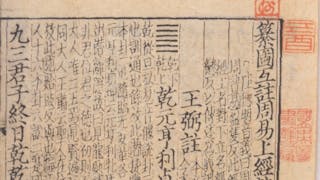
《荀子‧大略》:「《易》之〈咸〉,見夫婦。」

「亢,過也」,粵人所謂「過龍」,就是「亢龍」。

除了實際上用「色」(或「色仔」)指「色子」(「骰子」)這種賭具外,我們粵人還拿「色」來指其他六面體的物件,如「扭計色」(魔方)。

粵語「千祈」,即普通話的「千萬」。如「千祈唔好信渠(佢)」即「千萬不要相信他」;「千祈要小心」就是「千萬要小心」。

至遲宋朝,「快脆」一詞已見於文獻,而傳承此詞的,至少有廣州話與福州話。

我們粵語說到「無可比擬」這個意思時有「無倫」一詞。如說︰「好到無倫」、「精彩到無倫」、「衰到無倫」等。顧名思義,「無倫」就是「無與倫比」的意思。

其實既有「烏七八糟」及「污七八糟」就不可能沒有「烏糟」和「污糟」,因為「烏七八糟」及「污七八糟」顯然就分別是「烏糟」和「污糟」的「鑲嵌格」!

我們有「一物治一物,糯米治木蝨」這樣一句諺語。我們這句諺語中的「治」是「制服」的意思。類似用法,普通話只用於「害蟲」,而不用於人。然而粵語卻可以說「某甲治某乙」。

究竟是粵語「數」接近古語,還是普通話的「數落」和「數說」接近古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