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往,成績好,就會在教育體系裏面順利上升,不斷取得更高的學歷,也因此在工作裏面,步步高升。學歷、地位、收入,是緊緊相扣的。但是在一個人漫長的四五十年工作生活裏面,學歷佔的重要性愈來愈低。

從現代社會的觀點看,社會是多元善變的,「一紙文憑」已經不足以讓人「一帆風順」。學生不能只懂得讀書,必須要有更多元的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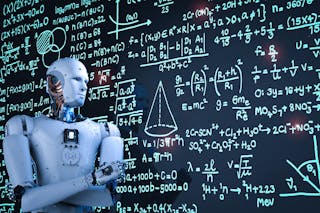
人與人之間的聯繫,愈來愈趨於個人化。在這種情形下, 科技的發展,逐漸把人際關係,尤其是與工作有關的經濟活動, 從機構為基礎而變為以虛擬空間為平台。

在學校學業成績高的,並不一定表示他們有其他處世的能力。相反,學業成績低的,並不代表他們沒有其他方面的潛能。

很多教育界的朋友,都有這樣的感覺:我們的教育體系,在不斷地讓學生感到自己是「失敗者」。這裏得說明一下,經歷失敗,也應該是學習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讓學生有自己塑造學習的空間。也就是讓學生可以定下自己的學習目標與方向,自己去探索學習的途徑,自己去制訂和承擔學習的成敗與得失。

知識建構,對於不是學術界的朋友、教育工作者、家長,最重要的一點:知識不是從外界進入人腦的,而是在人腦裏面形成的。

關於學習,尤其是學生的學習,大概有幾個問題是要經常問的:學習的內容:學些什麼?學習的原因:為什麼要學這些?學習的目標:怎樣才算學會了、學得好?學習的過程:學生又是如何學習的?

教育體系的演化,使得我們的教育,只有短期目標。人們把文憑當作能力,把分數當作知識,把教育體系裏面的晉升(升學),作為目標。

當「一紙文憑」的框架不再符合社會的發展,簡單的「可數」性測驗不再足以表達學生真正的學習所得,「分數」就不再可以成為可靠的學習指標。我們的教育,就是處於這樣的關口。全球都在掙扎。

在中國,很多科技的突破,是因為國家有明確的方向,機構、人員、資源,都是按照國家的方向而全面安排。

最近數年之間,許多民間的「集團辦學」如雨後春筍,許多與傳統不一樣的學校,遍地開花。許多國外的學校,都在中國辦國際學校(不招本國學生)、中小學的國際班、雙語班。

佔據着立法會議席的各個黨派:在電視機面前看來理直氣壯,甚或殺氣騰騰,心中可有香港發展的藍圖?很多事情也許都值得反對,然而,反對之餘,可有想到需要推動什麼?

全球幾乎所有國家,都在謀求教育的變化,都在應付社會群眾對教育日益增長的不滿情緒。但是,也可以大膽地說,真正找到大家認為滿意的教育發展方向的,也是絕無僅有。

玩具的生產,已經幾乎完全給商業行為左右,一些很有教育創意、根據學習原理設計的玩具,在市場上難以躋身。為了孩子着想,只有把防線退守到家長身上,好自為之,不要讓孩子泥足深陷。

為什麼在這裏要不厭其詳地講個人的經歷?因為這是筆者逐漸明白社會變化的途徑。與其說是研究方法,不如說是學習過程。

「教育的最終目的—學生的未來;教育的核心業務—學生的學習」。一個宏觀,一個微觀。這是筆者學習心得的最簡概括。

講求穩定的職位,已經不是年輕人考慮工作的主要準則。而事實上,常期穩定的職位,已經愈來愈難求。

現在,在後工業社會,機構的結構鬆散了。社會不見得會平等了,但是社會的卻沒有了嚴謹而固定的結構;也就是說,人們的機會平等了。

從教育的角度看,假如我們還深信我們少數科目的獨木橋,足以讓年輕人迎接未來、度過一生,我們其實是在剝奪他們在未來生存和成功的機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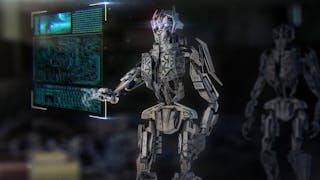
我們值得思索的是,科技的不斷發展,到底會為人類帶來什麼影響?好的是什麼?不好的又會是什麼?

現在,進入「後工業社會」,人又進一步被釋放了。負面的是沒有了可靠的保障,正面的是個人更自由了。面對紛亂的社會,人們愈來愈需要「自求多福」。個人也需要變得更加堅強。

近年經常聽到許多教育界以外,尤其是工商界的朋友,談到對於年輕人的期望,都會提到一些知識與技能以外的元素。其實,在人類的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把人的素質,局限在知識與技能。

年輕人逐漸離棄穩定的職位,走向小型單位或者個體工作,並非純粹一個量的問題。工作的性質與崗位上的要求,也已經很不一樣。

有人認為年輕人浪費了大學的資源,更有人怪責現代年輕人不濟、敗壞、變態。筆者認為,這是把今天的年輕人,放在一個昨天的社會來考慮。今天的社會、今天的機構,已經變得很不一樣。

社會變了,對於教育的期望也變了。不難看到,今天的年輕人,他們的職業途徑,與二十世紀的典型職業途徑,很不一樣。

一位北師大的教授說,大灣區的特點,是很多移民社會,因此社會文化比較講究包容。照這個說法,香港是中國與國際的一個接合點,大灣區又恰好是香港與內地的一個接合點。

受教育愈多,未來收入就愈高。假如每一個人都念了大學,是否每一個人都會有同樣更高的收入?又或者說,每一個人都念了大學,是否社會就平等了?

大學入學仍然會是一個競爭入學的境況。只不過美國的大學,似乎普遍地覺得,若只看考試成績,會不利於在中小學由於家庭資源不足而成績不佳的弱勢學生。

40多年前的社會、當時的大學畢業生、當時的大學教育,都難以用來衡量今天的事物。因此,作為政府,應該是運用社會資源,盡力照顧弱勢子女的青少年學習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