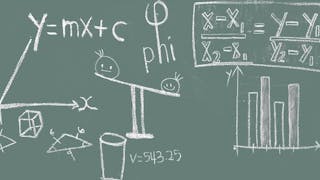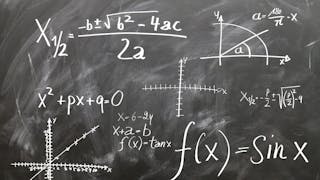教育發展與教育政策的關注點,主要是社會需要的人力資源;而人力資源的核心元素,是在工作上用得上的知識與技能。這也可以說是美國「二十一世紀技能」的基本框架。

真正為年輕人的未來着想,真正為他們提供公平的學習機會。我們可以從芬蘭學習的,太多了。

現實是各地社會普遍嚴重撕裂,教育的政治化,並不一定是因為政府。假如把品格教育處處拉進政治的框架,就無法有真正的品格教育。

只要不走回頭路,不會因為一些無聊的堅持而在一些無關宏旨的細節上糾纏,香港的教育可以闊步前進。其中一個關鍵的元素是預算報告提到的「專業領航」。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不只是埋頭做研究,也運用自己的科學權威,做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最近組織一個聯盟,研究如何發揮學習科學的現狀和潛在作用。

學術的發展,需要寬鬆的環境,給真正的學者予心無罣礙的環境和條件。已故學術巨人饒宗頤,因日本佔領中國,滯留香港,因而避開戰亂和文化大革命,於是香港成為饒公得以心無罣礙的福土。

筆者的肺腑之言:看學校,不是看本地,還是國際,也不是光看升學業績,主要看辦學者有沒有理念。學校深度的內涵,可以有天淵之別,對孩子的一生,影響極大。而沒有內涵的學校,頗不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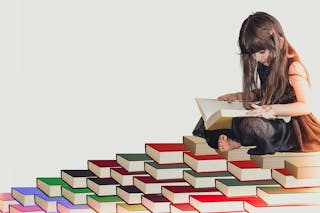
學生的學習,除了有動機、有選擇,還應該有自己的天地,自主地決定自己的目標、內容、過程、成果。

杭州市政府在市郊銀湖區建設一個吸引高級人才進駐的經濟基地。從學校入手建設經濟,也算是一種新思維。

訪問過杭州市的學校後,不能再認為內地的發展只講硬件,軟件的變化正在悄悄地發生。也許是蘇杭的特色,辦學正在走向細膩,也是正在悄悄地嘗試離開應試。

內地政治敏感的禁區不少,但是禁區以外,人們開闢的天地愈來愈大,特別在教育上,提倡新型辦學、網上教育、學習個人化、研學旅行等政策。這些政策都是香港沒有的,十分驚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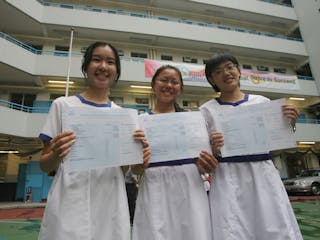
今天的考試,不管校內校外,幾乎都有時間因素:鬥快,慢了就失敗。其實不合理,因答得快的,並不一定表示學得好。

其實學校裏面也在作着不同的掙扎,不少學校和教師正在逐步掙脫制度的局限,努力為學生創造寬闊的學習環境。但是,制度和觀念不變,這種掙扎就會長期延續,也會耗費校長和教師們很多的精力。

課外活動稱為「課外」,英文有"extra"的字眼,多少有點額外的意思。由於正規課程將來是要應付公開考試的,而「課外活動」則有點可有可無,不是為了點綴,可以有更好,沒有也無傷大雅。

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作為家長,不得不留意這種變化。要青少年純粹乖乖地埋頭啃書本,也許與時代脫節了。大學收生也須要考慮這個因素。

工作與社會是多元燦爛的一片大洲,學生本身也是多元燦爛的一片大洲,偏偏連接這兩片大洲的,卻是一條狹窄的獨木橋──也就是教育。

中國也有少數民族的優惠政策。以前說的「老、少、邊、窮」,其中的「少」,就是少數民族地區。除了財政補助以外,近年扶貧的政策,正在迅速轉向發展經濟,例如鼓勵發展旅遊,因而發展民宿、農家樂。

中央民族大學成立於1951年,就是專門為面對少數民族而設立的。這裏教師的說法,中央民族大學的特點,恰恰就是不迴避差異,而且特意承認差異、突出差異,但又致力於差異之間的共融。

近年到俄國的次數不太少,但就莫斯科而言,以往都是開會、講課,完了就走。這次有機會到學校看看,與有抱負的教育工作者有數日的交往,可以說是對俄國的印象很不一樣。

「社會變了!教育也要變!」這種基調,是當時經過接近一年關於「教育目的」的諮詢,收到超過4萬份意見書以後的主要結論。這次在莫斯科,卻還是不斷在思想上受到衝擊;以上的基調,也得到很大的充實。

「教育2.1」於去年11月舉行過一次「大教育」的大型交流研討會,之後逐步形成「大教育平台」,參加的企業和機構愈來愈多,漸成風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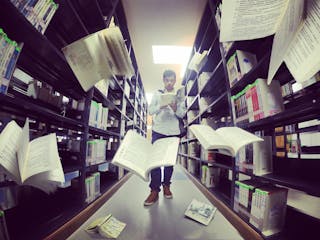
無論機器智能的發展,還是對大數據的認識與使用,香港都正在迅速墮後;而對於下一代的教育,更似乎不在我們的雷達網之內。

教師與學校站在風浪前線,他們比任何人都關心身邊年輕人的成長。社會應該站在教師一邊,大家如到學校看看,就會看到絕大多數的教師努力在實現自己的使命,而不是從事政治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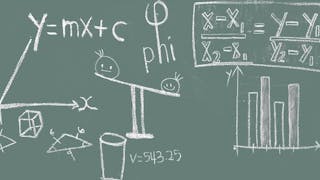
香港教育局在2005年頒行的學制改革行動方案,打破文理過早分家,而提倡「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因此有綜合科學科與綜合社會科,讓所有的學生都有一點理科和社會科學的基本知識。

聖保羅的歷史證明,洋人辦的學校、洋教會的學校,從另一個角度看,其實在東西之間、傳統與現代之間,築起了一道橋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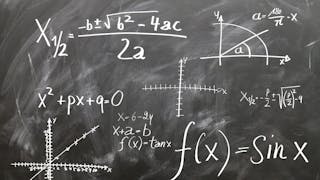
香港發展科學教育,目的是什麼?目標是什麼?是為了使用科技?香港人對於使用新科技、適應新科技,不在話下,從來可以說是得心應手;在年輕人來說,更是比大人要學得快、學得多,似乎也毋須勞動到教師、學校和家長。

香港的大學教師投訴科學及工程學系的學生缺乏堅實的理科基礎知識,未能應付理工科的要求。可幸的是,四年制大學有着額外一年的時間,可以讓有志求學問的學生彌補理科根柢的不足。

課程改革增加了學生的學習經歷,拓寬了學生的視野,但是科學學習有點被削弱;小學的常識課,自然科學的內容較少;由於大學收生條件的變化,許多高中學生只念一門科學;即使是看傳統的科目,理、化、生的教科書遠遠追不上日新月異的科技發展。

現在的競爭是從「能否升學」轉移為「能否升入最好的大學」。學生心裏面也有一個梯度、一種檔次,由高到低:資助的大學、外地的大學、高級文憑、副學士、職業訓練局等等。這種狀況,必須改變,應該重新定義高能教育。

一直以來,學校都感到人力不足,政府也會間歇性地增加學校人手,但是看來要解決的是根本的概念問題:學校到底承擔什麼工作?教師又擔任什麼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