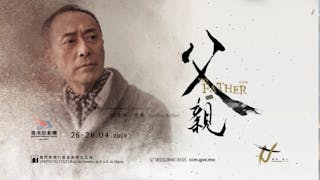我和香港電影美術學會前會長雷楚雄相識20多年,有很多共同朋友,每次見面,搭對「三八」線,開心至死。

香港的舞台藝術活動,大部分是政府出資。我為政府服務20多年,主責協助「派錢」,哪好意思拐過彎,反問政府拿錢做藝術,如果用自己和朋友的錢,當然要考慮市場,所以,我歸納musical為「市場藝術」。

楊立門自小愛唱歌,中學在高主教書院,已組band。1982年,大學快畢業,他參加TVB新秀歌唱大賽,但參賽期間,政府取錄他做「AO」,為了穩定生活,遂退出比賽,不當歌星。

港龍的黃金期,和我是同一步伐的,我怕長獃於一個狹小空間,只有坐上港龍,我的不快會全消;可惜,今天它走了,我也只能追憶似水年華:幸福的歲月便是失落的過去。來,和我追尋過去35年的港龍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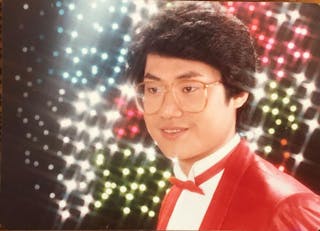
坊間視為「好口才」的人,許多其實是語言惡棍,他們口若懸河,誤導大眾。在影視圈,有一位藝人躬行實踐,由1976年至今,靠口才「搵食」,他是司儀鄧英敏。

眾惡男中,我和「卡拉之星」棠哥最投契,首先,年紀相若;此外,在年輕人愛「夜蒲」的八十年代,棠哥在disco做管理,是大家熟悉的朋友。那時候,他是高大俊男一名,身邊美女如雲,曾經非常風流,幸好修成正果。

生命,包括生理和心理,如威化餅,本來脆弱,只不過有人「出事」,有人沒事;健康的你,該感謝幸運,珍惜眼前,切勿歧視傷殘人士。傷殘,包括精神健康受損的,需要大家打氣,送上尊重和關懷,這樣,香港才溫暖。

《麥路人》只是一部以社會問題為題材,並非深究這問題的「情緒影片」,它的思考價值不高,手法保守。我們常批評,電影不要像電視劇,但是《麥路人》太像溫情電視劇。

我們這些中年人,常常對着新一輩搖頭:疏懶、缺乏大志、諉過於人,大學畢業,還叫父母安排工作、支付婚宴、買房子。他們恐怕要刮骨療毒,才可醫治這種「脊椎彎」症。

陳美齡談音樂和教育,恐怕太多,我要改變話題,談大家心目中的「潮都」:東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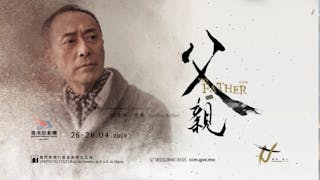
能「得道」,極不容易,要三世修行,五世為人,且看香港舞台藝術的台前幕後持份者,能否把握良機,在一番努力後,十年以後,「不雨棠梨滿地花」,在外國、在大灣區,都排滿香港的舞台節目。

有實力的年輕音樂人,要自行製作和發行音樂來打造市場,而那些屬於「娛樂圈」的歌手,只好繼續依靠唱片公司的人工包裝。

我愈想得多,思路愈紊亂;終於有一天,遇到電影老行尊,香港電影發展局前秘書長馮永,和他來一次思想切磋。

畫是靜態的藝術,卻反映動態萬物的美,平面的畫,看似平凡,其實發出不平凡的電波,碰觸心靈。

靠文化藝術吃一碗飯的同道,吃半碗飯的我,常常懊惱空間有限,想往前發展,步履維艱;不過,很多這個圈子的老朋友,數十年來,雖然沒有春光明媚,但是日子又總會過去,起碼,活現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