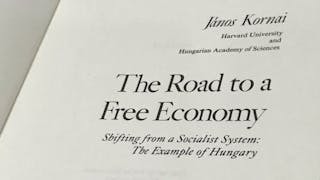美国矽谷的創業投資作為一個生態系統,有兩個大流派。如果前面的一派是自由派,第二派就是實務派,他們實施財務控制,頭腦清醒,有接地氣,是現實主義者。

美國西岸的矽谷之所以在上世紀70、80年代,打敗如日本的芯片工業群和美國東岸波士頓的資本創投群,與矽谷風投界的人與人,跟公司與公司之間一種獨特的弱連結有關。

收購合併是企業外延發展或起死重生的手段,千禧年初由於大數據開始普及,憑藉多組數據庫和統計程式,提出了嬴家詛咒的説法。只是,當局者和旁觀者各有各忙,似未有同識。

追源遡古,美國的併購業或可從19世紀的約翰.摩根在銀行業、鋼鐵業和鐵路業的合縱連橫始,一浪接一浪,到2020年代,起碼有6、7次的潮漲潮退。

這株夾縫中的小花,盛放時是艶麗的洋紫荊,風雨交加時就是荊棘滿途。然而,風中勁草的生命力,在雨過天青後的艶陽天,自能一展英姿。

由民間舉辦的商務會議,如能及早在香港復辦,對本港、大灣區以至內地,都會有很大的輻射作用的。

關於星港雙龍爭輝之説,多以狄更斯的《雙城記》來比喻;但不才卻想以港式俚語「代客泊車」來形容。

人始終是人,在生活行事上有許多的習慣和系統的局限,讓光陰不斷地從手指罅隙或瑣碎夾縫中枉然流逝。

資產的一買一賣才是股權投資人的技能和專業職稱,持有期當中的附加值當然也很重要,但每當當事人成為當局者後,就經常會有角色混淆,墮入外行人管內行人的誤區。

金融資本主義成為西方社會建造全球化時的尚方寶劍,當全球化浪潮,席捲亞洲大大小小的經濟體時,起先的確是措手不及,但在長視角之下,亞洲諸國是否輸家?金融大鱷是否贏家?

大學生要麼想當大企業的高管,四處出差搞併購,要麼是以推動小眾議題為職業,甚至是終生使命,沒有太多人會想站出來做公務員或國民領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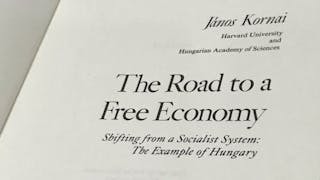
科氏是從二戰中猶太人被大屠殺的經歷中逃生出來,沒有正式上過西方經濟學的課,對許多經濟現象的觀察和總結,是他天真的、自然的經驗結晶。也許因此緣故,放在今天的時局中,仍然拳拳到肉!

超過半個世紀以來,天天都蹲到田間,照顧他最親密的情人,那一支支水稻,雄性的、雌性的、野生的、人工的,和它們的孩子,各種各樣的稻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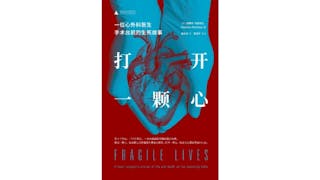
譯者的文筆,不只要傳意,還要傳神,很難呀!是哪本譯作讓本文作者「幾乎要邊讀邊用手遮擋」又開心地讀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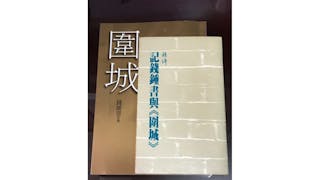
《圍城》是一部非常難得的作品,是「癡」、「笑」、「博」和「悲」的結集,現在想來,難出其右。

機械人取代愈來愈多人類的工種,十年前取代的是工廠工人,今日連許多白領的中高層管理人,都丟了飯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