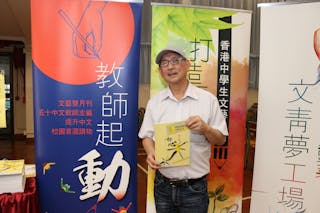眼前的恩神父,令我想起了明朝的利瑪竇,400多年前,年輕的神父,為了傳教,遠涉重洋,來到陌生的中國,迎接他的是因百般誤解而生的敵意。恩神父走的,何嘗不是利瑪竇走過的傳教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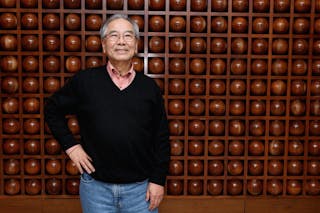
榮鴻曾自言是個幸福的「中間人」,在科學與人文;中國與西方音樂;香港與美國;精緻古琴與通俗南音板眼之間,游走於不同的領域。

訪談那天,天下着雨,我跟攝影師一起跑到榮鴻曾教授下榻的酒店,跟他聊了幾個小時,內容當然離不開地水南音,還有粵劇和古琴……

莊梅岩強調「在劇本中,人物最重要,甚至比主題、布局更重要……」在心理學方面的訓練,讓她對人性的認識更多。她愛上編劇,是因戲劇可以「觀照人生」!

對於粵劇藝術,羅家英的個人取向就是──「堅持」。所謂飲水思源,一路走來,他靠的是華光師父賞飯吃;今時今日,他要回報華光師父,積極推廣粵劇這門本土藝術,並致力培養新秀,期望粵劇能開展出新的天地。

阮兆輝認為藝術有不同的派系,大家要包容,但千萬不要將基本的東西連根拔起──這就是他的「微願」!

國家一級導演、中國舞蹈藝術突出貢獻舞蹈家丁偉,一直嘗試將少數民族的傳說故事,改編為舞劇,他擅長將傳奇人物置於日常生活中,在舞台上呈現他們的喜樂與悲苦。

現為敦煌研究院特別研究員的李美賢老師,談及自己從入門而成為敦煌專家的經歷,全繫於一個「緣」字。

李美賢老師有感於很多藏家,百年歸老之後,所藏珍貴之物,都散迭無存,實在教人感到惋惜。她期望「收而不藏」,將蒐集的文物,公諸同好,在有生之年好好利用,藉以弘揚中華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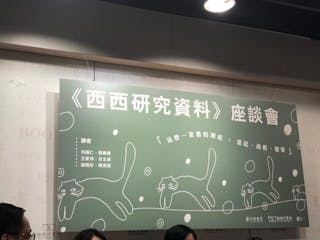
前幾天,接到何福仁的電郵。傳來10月8日西西獲得第六屆紐曼華語文學獎(詩歌獎)的消息。她是這個獎的第三位女性獲獎者,也是香港首個獲獎作家。

香港藝術館館長司徒元傑作為展覽策展人,一般人視之為職業,館長卻視之為事業「這不是一般工作,而是不計較,講心、講理想,做好之後,有一份滿足感」。

展覽的目的就要將藝術作品介紹出去,讓大眾了解、欣賞。藝術家透過慧眼,將紛紜世事,加以組織、沉殿、昇華,創作成藝術品。策展人就是要將作品「拆解」,用深入淺出的手法、立體的角度去展現作品的特色。

2018年11月9日是豐子愷誕辰120周年,豐子愷最疼惜的么孫,豐羽覺得有責任為爺爺做點事,弘揚豐子愷的藝術,是他一直以來的想法,於是決定在香港舉辦豐子愷作品展。

推動學生的人格教育,是鍾玲的目標;培養對社會有承擔,富有人文素養的學生,是鍾玲的理想。

當年念近代史,「九·一八」事變已如烙印般,鑴刻心中。想不到,多年後,竟然有機會來到瀋陽,踏足在這個地方。

作品與評論之間的連繫,可謂千絲萬縷,張秉權指觀眾是戲劇演出的一個必須部分,沒有觀眾,作品便是失去意義。觀眾認真去看戲,將觀後感寫出來,其實是將戲劇的生命延長了,所以劇評也是一種創作,有獨立存在的價值。

3,000多年以來,草原上的遊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民族之間,既有不少衝突,亦有融合之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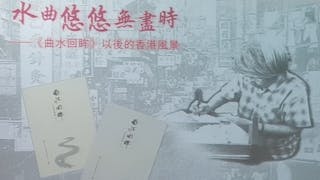
當天的小思老師,其實患上感冒,但她不願意改期,仍堅持出席。擇善而固執,素來是她的價值取向,認真而用心,亦是她的處事態度,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認識陳冠中的文字,當然是從《號外》開始,那時剛念完大學,喜歡看《號外》。若論面對面暢談,倒是第一次。

走過文壇幾近一世紀,劉以鬯先生為我們帶來「與眾不同」的文學作品,他以小說書寫生命,把自己的時代、自己的記憶、自己的詩意……全留在作品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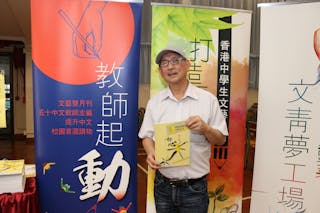
在《教師起動》的創刊語中,關夢南明白道出「香港辦雜誌難,文學雜誌更是票房毒藥」沒有天時、沒有地利,幸而有的是「人和」──「大部分的中文老師凝聚起來,卻是一股沒有人敢輕視的力量。」

陳慧感慨,從「自由行」開始,她已淪為「異鄉人」。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竟成了異鄉,熟悉的建築物被拆卸,熟悉的語音也聽不到,一切都變得陌生。

在香港戲劇界,毛俊輝這個名字無人不曉。在2005年,他已獲香港演藝學院頒發榮譽院士,2014年再獲演藝學院頒授榮譽博士。去年又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傑出藝術貢獻獎」,可謂實至名歸。

毛俊輝的父親原是位油畫家,他遺傳了乃父的優良基因,在美術方面也很有天分。不過,毛俊輝志不在此,他最愛的是演戲,故鍥而不捨,努力爭取演出機會。

外型像一彎新月的貝加爾湖,是一個天然的淡水湖,也是世界最深、最大、最古老的湖泊,自古以來,一直被視為是神聖之海。

三天的北韓之旅,比走馬看花還要差一大截,簡直就是霧裏看花。

魏時煜喜歡拍紀錄片,因為可以不斷有新發現,「我覺得紀錄片比較過癮,因為拍紀錄片的時候,每次發現一些新的材料,一張新的照片,一個新的人,一種新的組合方法,都會帶來興奮……」

魏時煜在訪問過程中,感受到何秋蘭與黃美玉這對舞台姐妹不想對古巴革命多作評價,彷彿革命對古巴華人真的沒有影響。

丁新豹博士讀書時,接觸藝術。畢業後從事藝術工作時,認識歷史。到歷史博物館工作時,有意推動歷史教育。儘管身份多變,但文化之心不變。

許鞍華在電影界經歷多年,在藝術追求上,她已有所改變──「我現在對鏡頭、燈光、色彩等,已沒多大的興趣。我覺得電影的『調子』很重要,將現實生活中無以名之的感覺拍出來,讓觀眾產生共鳴,那才是好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