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語言文字的文化多元,應該也可以成為一種難得的資產。香港處在中西文化交匯之點,中英語言的並用,又是粵語與普通話的交叉點,非常寶貴。

朱師傅是世外高人,難得有緣成為他的忘年交。當年我每周都約他在九龍灣德福商場的仿膳飯莊吃午飯,親自拿他的手稿,每次見面都相談甚歡。

經過兩年多疫情的洗禮,中大校園再次煥發姿彩,祝願母校一甲子校慶再攀高峰。

翔鐘身為老總,與香港名人時有接觸,和曹仁超兄一樣,觀察很貼地氣,也不是人人有此體驗。如今二兄俱往矣,能不惘然。

邱先生循循善誘,是位敦厚長者,喜歡跟同事聊天、打成一片,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邱總很關心後輩。

6月21日午夜收到邱翔鐘夫人電郵,驚悉在倫敦的邱翔鐘先生逝世,邱先生與我相知相交37年,悲慟萬分,徹夜無眠。來世上一回,億萬人之間,與這樣一個難忘的師友同行了半生,地久天長之間,如此短暫,真是捨不得。

江迅1994年移居香港,加入《亞洲週刊》擔任資深特派員,以他在內地文化及新聞界的深厚資歷,很快就嶄露頭角,闖出名堂,很多獨家報道挖出鮮為人知的內幕消息。

美籍印度裔的資深傳媒人褚簡寧(Michael Chugani)辭任無線電視明珠台的時事節目「清心直說」(Straight Talk)主持,並停寫《南華早報》、《信報》專欄。

七十年代香港出現了至少兩位「姣婆」作家,「她們」每天在報章寫中區白領麗人如何「姣屍炖篤」、如何煙視媚行,寫得出神入化,吸引無數狂蜂浪蝶,成為報壇佳話。筆者有緣認識這兩位「中區白領靚女」。

幾經斟酌研究,我們把公司願景定為:建立一個優質媒體平台,在大中華地區發揮影響力;使命有三:一、為讀者搜羅優秀作家;二、為優秀作家提供理想寫作平台;三、為社會長遠發展貢獻真知灼見。

這位George,是我心中獨一無二的George。故人逝,自是悲傷,但他留給我充滿正能量,想着也會微笑的美好回憶,相聚的愉悅多於永別的哀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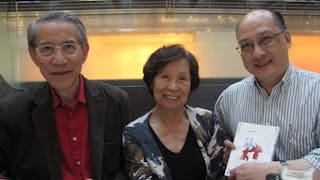
《信報》的樂評,其實是沈鑒治的「今生」,至於前世,則原來早在五十年代已經開始,絕對是香港音樂評論的先驅。

在《信報》共事時,因為各有各忙,接觸雖不算多,卻從無疏離隔膜的感覺。退休後,彼此時有相約外遊,談新說舊,分享同行樂趣;今讀沈兄自傳,箇中人事,並不陌生,除了興味盎然,更能喚起前人詩作的情致。

陳明銶教授去世後我負責約稿及編輯紀念他的追思錄,知道更多關於他過去的事情,他對每一位學生與朋友都真誠付出,來者不拒,盡心盡力,燃燒了自己,照亮了許許多多的後輩,我受益極多,感恩不盡!

本社作者、國際時事評論家、作家、翻譯家關愚謙教授因病於當地時間2018年11月22日在柏林離世,享年87歲。本社刊登張建雄先生懷念關教授文章。

林先生的一些寫法確實感性,例如他預期1997年7月1日 會有「百官悲送」的場面,事實上,到了主權移交當天,「百官」 是去了會展中心出席回歸儀式,沒有「悲送」。

「這本書的英譯本得以出版,我希望不是因為家父的社會地位使然,而是一位至今仍然筆耕不輟的作者,系統地探討香港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對不對都完全呈現,沒有逃避,沒有隱瞞,這很難得。」

當年要是真的那樣立法,我們感到言論自由便很有問題,洩露國家機密的界說也觸目驚心,讓人不知所措,那是與媒體工作有切身關係的問題,所以林先生不止在文字上提出質疑,他和我還是唯一一次跑上街頭表態反對。

英國人決定撤走,我們唯有接受現實,希望延續近乎英治時期的行政制度和管治。

據我們多年的觀察,英國人的管治,特點就是他們有足以專制、專橫的條件一意孤行,斷然行其所是,但優秀的是,他們往往會在最後關頭順從民意民情,不走極端。

「《信報》開辦一年左右,那是最艱難的時期,籌備階段訂購的印刷機器運到港要付錢,香植球先生在大跌市中賣股票幫我們。」

他較筆者年長不太多,但其人生歷煉肯定把我比下來,尊稱他為「曹生」不是因為陌生,而是一份衷心敬意呢!

他較筆者年長不太多,但其人生歷煉肯定把我比下來,尊稱他為「曹生」不是因為陌生,而是一份衷心敬意呢!

曹Sir雖然走了,但他對事對人誠懇的態度卻常留心間。

他說沒有什麼嗜好,最大興趣是投資賺錢,不過他從不吝嗇計較,對我們都很慷慨。

曹先生決定停筆後,我和幾個同事商量過找誰頂替。我的意見是:要找一個人去頂是不可能的了。

人人慨嘆蝸居難求,曹仁超覺得最可悲的是,香港人最大的願望竟然是買樓收租,包括大學生。「即使好運或者憑父蔭,25歲前儲到首期,開始供款,供到45歲為止,到時都不用想創業了。所以我經常寄語年輕人,不要讓500尺綁住你的青春。」

從1990年加入傳媒至今,25年來我最關注的議題始終是高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