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人佔領這個小島,並建立『香港』這個殖民地之前,香港並不存在。所以,『香港』本身就是一個創造出來的東西,是一個由想像變成真實的過程。」董啟章道。從虛無變真實,成為董啟章建構香港,或是維多利亞城的主旋律,讓城中人或過路客都為之驚豔,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王德威便是其中一位,他說:「我敢說,在中國即使到今天,沒有一個像董啟章這樣的作家。他具有特別的視野,而這名叫董啟章的作家開啓了這種寫作模式。書寫香港這本身帶有標誌性色彩。」(註1)這不禁讓人好奇,這是一個怎樣的香港?與我們切身處地生活的香港有多相似?
虛構的維多利亞城
「在歷史的必然面前,小說無可作為。既不能去質疑它,也不該去附麗它。」董啟章在《地圖集》的後記中寫道,於是他開始遊走在歷史和想像之間,用想像來建構屬於他的維多利亞城。
維多利亞城的傳說,令我們面對一個考古學的問題:如何證實一個城市的存在?〈海市〉,《地圖集》(P.62)
「一般來說,人們認為像考古、歷史等相關的文本,是屬於真實的範疇的。但是,作為說故事的方式,它們有構成的過程和方法,並不一定能做到完全客觀,當中必然有事實本身以外的因素參與其中,加以影響。我感興趣的,就是這些因素。」這些因素成為小說中不同的敘事立場,暗示某種價值判斷,這可能離我們所認知的小說故事有點距離,但對於英國文學和比較文學出身的董啟章而言,把這些跨越傳統文學類型的作品理解為廣義的「小說」,即英文的fiction(「虛構」)更為貼切。
虛構,是維多利亞城,乃至所有城市的本質;而城市的地圖亦必然是一部自我擴充、修改、掩飾和推翻的小說。<維多利亞之虛構一八八九>,《地圖集》(P.75)
董啟章選擇這個創作立足點在香港文學甚至華語文學的脈絡中是新穎和少眾的,讓他成為香港文學的脈絡中一個無法安放的角色,哈佛大學榮休教授李歐梵更將董啟章稱作異數。正是這樣的特立獨行開展了新的小說觀感:「讓小說跨進知識書寫的領域,也許可以讓我們對最廣義的故事──歷史,有全新的理解和體驗。反過來說,這也可以更新我們對小說的期待,為小說寫作開拓更大的創造空間。」
歷史消亡後 用想像再築城牆
懷舊並不是指向歷史,而是指向歷史的消失。──也斯
「當然,今天我們再來想像,並不能還原當初的真實,但我們去了解想像本身,是十分重要的。」他道。那當初的真實何在?很可能是不存在的,在董啟章眼裏,歷史是「最廣義的故事」,套用也斯一句話也許說的更明白一些:「懷舊並不是指向歷史,而是指向歷史的消失。」(註2)在《花樣年華》中張曼玉旗袍的花色有種沉着的豔麗,昏黃的濾鏡是我們心心念念「舊」的標誌,不見得當時真實的光景便是如此吧。隨着真實的八十年代愈趨模糊,便成為也斯口中「歷史的消失」,留下的便是我們對那個時代的「想像」了。

想像不只是許多人對過去幻化的魔術,更是董啟章建構他眼中的「香港」的一磚一瓦:「我們了解過去是如何想像出來的,可以幫助我們想像今天,並且想像將來。」這種想像更進一步是圍繞着身份認同的問題,在董啟章看來,這種身份迷茫帶來的想像有別於「尋根」,是殖民地失根飄零一族的專屬:「馬華作家黃錦樹和黎紫書也有類似的想像。也許,這種想像只存在於曾經成為殖民地的地方的文學,因為他們的身分源於虛構或創造,然後經歷失序與尋找。」大陸文革過後的尋根文學,從韓少功一篇<文學的根>開始,阿城、賈平凹、路遙和莫言等作家紛紛用自己的文字踏上尋根之路,董啟章認為兩者在根本上有些區別:「大陸作家也曾經尋根,但他們的根早就在那裏,至少他們是如此地相信。但是我們其實沒有根。」
靠想像重組歷史,還是自我放棄?
「尋根」說白了是一種身份認同,本身涵蓋很多因素。斯圖爾特· 霍爾(Stuart Hall)對建基於定位和異質的「文化身份」的論述中提出,文化身分是恆常處於浮移、變動、再造循環的過程中,會因應歷史、文化、政治、經濟等社會因素的發展爾蛻變。洛楓從這個角度看《地圖集》指出,當中「歷史的想像」透過「重寫歷史」的方案,以小說的藝術形式再造香港「文化身份」的內容。(註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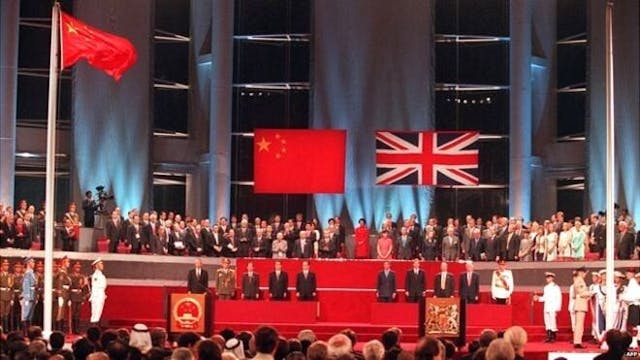
承接上言談到的「尋根」,董啟章認為對香港人而言,這可能是緣木求魚:「香港人的文化身分認同,如果用「尋根」的方式去處理,是沒有結果的。」他談起《地圖集》裏面有一章<地質種類分歧>以奇想的方式談到,有兩派地質學者:「一派主張香港的本土性來自於市區範圍的地質,也即是淺層的沉積物和堆填物。另一派主張深藏於地底、年代久遠的火成岩或花崗岩,才是這個城市的根基。這是兩個追溯根源的觀點,兩者都好像有自身的理據,而且互相排斥,針鋒相對。」
而相對於碩大如皇皇大地之母的花崗岩,沿岸那一小撮堆砌而成的土地,便變成了邊緣中的邊緣,在渺小中更見渺小。它甚至不是任何一個地質紀的產物,而是短短百年間由傾倒廢料而形成的垃圾場。在這種「本土」下面,又尋得出什麼樣的根呢?——<地質種類分歧>(P.146)
「我並不認為任何一方就是答案。因此,我想用形象化的方式,暴露出雙方的理據的片面性。所有的文化身分,都是『被發明出來的傳統』。」董啟章道。對於身份的困惑,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陳孟君對董啟章作品的處理有這樣的評價:「困惑於『我是誰』的港人,陷於日常生活的勞碌瑣務之中,遂安於習焉不察的名字,不再或無從理解香港故事被他者化的癥結。這無異於自我放棄:批判性地件事中英雜揉而成的記憶,致使無所憑依,失根又失家。」(註4)
董啟章和陳孟君都肯定了香港是沒有「根」的存在,不管是否曾經擁有。董啟章認為,對這個可能未曾出現就失落了的「根」可以這樣處理:「與其尋根問底,試圖以此為據,不如確立,身分是一種基於相同的價值和理念所共同建構出來的東西。我們的尋根,其實是把根重新發明出來。這就是『歷史的想像』的意思。」
從台灣「回流」 堅持香港書寫
與香港毗鄰的台灣也有着殖民歷史,兩地在許多範疇上都有無形的呼應和相互輝映。問及作為香港作家,怎麼看香港文學和台灣文學之間的關係,董啟章開玩笑說:「我可以說是先在台灣出道,然後才「回流」到香港的。」董啟章1992年開始寫作,1996年出版長篇小說《雙身》,1997年出版《地圖集》,之後主要的作品都在台灣出版。他憶述:「我在1994年得到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可以說是加入了台灣的文壇。雖然不算十分積極地參與台灣的文學活動,但以出版和發表來說,在台灣一直有我的身影。跟其中一些作家如駱以軍也比較熟,感覺是同代人和同路人。也許,我的台灣讀者人數比香港讀者還要多一點點。」即使在台灣「出道」,董啟章認為書寫香港題材才是他的特色所在,這點堅持亦深受台灣讀者歡迎和喜愛:「我甚至曾經寫了一部運用大量廣東話的長篇小說《時間繁史.啞瓷之光》,而一些年輕台灣讀者不但不覺反感,反而很努力地解讀當中的廣東口語。這應該可以說是真正的文化交流吧。」

談起台灣,總離不開「小清新」、「小確幸」等詞,儘管是近年才興起的新詞,但台灣文學和電影的發展脈絡、城鄉生活節奏等都是有跡可尋的;而香港頂着國際都市的闊邊帽,以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姿態與世界賽跑,贏得青睞,在高速發展的公路上馳騁,使得兩地書寫的題材、語言風格都南轅北轍。董啟章認為台灣文學跟香港文學相似度不算高,但可以彼此彼此互相了解的聯繫可能就在繁體字了。這點台灣作家白先勇在多次訪談中提過香港和台灣保留繁體字一舉是文化傳承的可貴之處。除了文字,董啟章提出兩地在社會和文化發展階段或有許多可以比對的經驗:「在自我身分和本土性方面,雙方也有共通語言和話題。香港和台灣的歷史經驗,表面上有很大差異。香港是英國殖民地,然後回歸中國;台灣經歷過日本殖民,後來又被國民黨統治,最後發展到民主選舉,民進黨上台。不過,那種身分的轉變,不同身分之間的衝突,也有互通的地方。到了現在,彼此最相似的,可能是年輕一代的困境,包括身分認同和政治自主,以及經濟上的低收入和無出路等。我不知道年輕一代的文學人有沒有同感。」
社會運動隔岸呼應 觸動年輕一代
我感覺到,自己跟年輕人之間出現了距離,沒法像之前一樣很自如和自信地寫年輕人的故事。
2014年,兩地先後爆發「太陽花學運」和以佔領中環見稱的「雨傘運動」。台灣年輕人群起反對黑箱服貿,香港年輕人也紛紛走上街頭高呼「我要真普選」,個個血氣方剛,無畏無懼地表達訴求,同一代人隔岸經歷的青春,也在兩座城的發展中,寫下長長的一撇,期待着後面蓄勢待發的一捺。

每人都有少年時,時間倒退30年,董啟章仍是走在港大文學院的走廊,捧着一摞外國文學作品的學生。歷史的推演不會放過任何一代人,董啟章畢業的時候正好遇上八九六四,他坦言對自己的衝擊很大。「當時我剛大學畢業,年紀跟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差不多。之前一直對內地的狀況沒有認識,也不關心,但因為同樣身為年輕學生,而被觸動了。那時候忽然產生強烈的認同感,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強烈地感覺到中國跟自己有密切關係。由此而來的激憤和悲傷,也是非常強烈的。」然而對董啟章而言,六四的衝擊有限,他形容是一種「大起大落」的感覺,往後十年的寫作歲月,在作品中踏雪無痕,而他的筆尖終在回歸後落到香港自身的狀況。

文學最廣義的定義擔任記錄的工作,誠然,香港文學也記載不少香港發生過的大事件,正如我們會在馬朗的<太陽下的街>讀到六七暴動的境況,會在西西的《我城》中看到菠蘿的蹤影。雨傘運動雖沒有出現在董啟章的作品中,卻無形間成為他寫作的轉折點:「我在雨傘運動之前,持續地書寫年輕人的社會參與,主要是描寫地區保育那一代人的故事,也即是所謂的八十後。雨傘運動冒出來的,卻是更新一代的年輕人。對於雨傘運動關於民主的訴求,我是認同的,但對於後起的極端本土主義,我充滿懷疑。我感覺到,自己跟年輕人之間出現了距離,沒法像之前一樣,很自如和自信地寫年輕人的故事。於是,我轉而回到自己的年紀的世代,書寫中年人的狀況。」
梳理歷史書寫 香港文學無法逃避的階段
到今天,這張力依然存在,甚至更強烈。這應該是這個時期的香港文學無法逃避的狀可能就是身分認同兩端之間的張力吧。這個張力籠罩着所有作品。我一直嘗試去了解它、駕馭它。到今天,這張力依然存在,甚至更強烈。這應該是這個時期的香港文學無法逃避的狀態吧。
雨傘運動在香港留下歷史性的一頁,在文學作品中當然多少有所着墨。雨傘運動三週年,有人漸漸淡忘當初的奮勇,慷概激昂,有人把握時間和機會加緊懷念,董啟章卻認為書寫這一章的時機尚未到來:「雨傘運動的影響正在浮現,社會對它的看法也會隨時間而出現不同的觀點。經過了激情和憤怒的階段,我們會看得更清楚。」對如此重要的事件,董啟章提出「不寫之寫」,更顯一種無法言表的重要:「對於重大的事情,我們要沉着,不用急於去寫它。又或者,根本不用去寫它,它的影響和意義也會在文學中浮現。有時候,沒有直接寫的,反而是最重要的東西。」

「歷史事件對寫作的影響,往往是深層的,甚至是潛意識的。」他道。每個人都是一個複雜的個體,精神心理有着無限廣闊的空間和世界,然而立身處世,社會或有許多衝擊和刺激,或拓寬,或成為無形的束縛,董啟章嘗試梳理社會、歷史和寫作的關係:「在六四與回歸之間,如果要說的話,可能就是身分認同兩端之間的張力吧。這個張力籠罩着所有作品。我一直嘗試去了解它、駕馭它。到今天,這張力依然存在,甚至更強烈。這應該是這個時期的香港文學無法逃避的狀態吧。」
註釋:
1.香港電台《華人作家》節目,<名字的玫瑰 — 董啟章地圖(上)>,2014年10月5日。
2.也斯:《香港文化》(香港:香港藝術中心,1995年),頁25。
3.洛楓:歷史想像與身份的建構,中外文學,第28卷,第10期 2000年3月,頁。
4.陳孟君:<地圖、神話與(偽)考古人類學:論董啟章小說想像城市歷史的路徑>,臺大中文學報,2015年第48期,頁161-213。
講座活動推介:
董啟章:繁華夢未醒
日期:2017年11月11日
時間:11:00-12:00
地點:中環下亞厘畢道二號藝穗會地下劇場
費用:$100
詳情:http://www.festival.org.hk/program/dung-kai-cheung-cantonese-love-stories/#more-6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