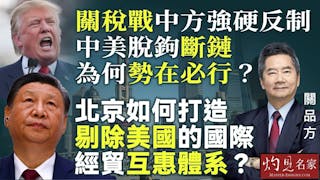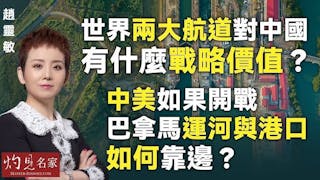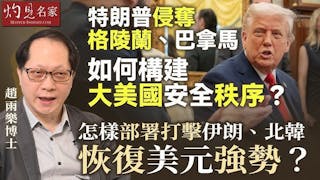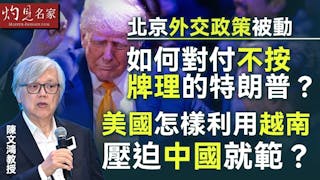從世界經濟歷史的發展和現狀來看,今天的中國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在實現本身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帶領發展中國家走出全球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困局,讓全球經濟在激發增量的過程中,平穩達到結構再平衡。長期而言,中國也有能力帶領非西方國家,針對全球治理與國際合作體制失靈的問題進行改革,以建構一個更公正、包容、有序與可持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這兩方面的內容都是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責任。同時,在國際責任的構架內,中國能夠避開西方和美國對中國的潛在圍堵,正面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從而實現長期的和平發展、民族復興的目標。在這樣一個時代背景下,絲綢之路才顯現其不尋常的意義。
國際秩序存在嚴重失衡
為什麼這樣說?首先,現有國際經濟秩序存在着嚴重的結構性失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既是這些失衡的必然結果,也使得這些缺陷暴露無遺。西方國家過度消費,政府舉債度日;美國濫用其鑄幣權,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動搖;全球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不斷增高,熱錢到處流竄,導致全球資產泡沫;國際自由貿易秩序,正被區域自貿板塊逐步侵蝕。
西方的結構性經濟失衡,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崛起有關。當代新自由主義於上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於英美國家的戴卓爾首相和列根總統時代。開始時焦點在於私有化和政府退出經濟領域。1990年代初冷戰結束之後,新自由主義很快就發展到世界經濟領域,主要是對經濟全球化的理想化,錯誤地認為全球化會形成完美的國際勞動分工,各國可以憑藉其比較優勢 ,來促進無限的經濟發展和財富的積累。看不見的手和比較優勢是古典經濟學的核心。不過,這兩者都促成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西方各國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經濟結構失衡的道路,主要表現在國內產業格局的失衡、社會性投資與生產性投資的失衡、金融創新與投機的失衡等,而最終則表現為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失衡。全球化、資本外流、就業不足、過度福利、弱政府等等,所有這些問題是西方經濟結構失衡、經濟和政治失衡的結果。這表明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又到了一個改革和轉型的新階段。最近,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危機討論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政治危機。到處蔓延的抗議浪潮,只是西方政治危機的其中一個表象。

金磚國家缺乏足夠實力
對西方來說,問題的核心是如何重建國家權力秩序?西方花了很長的歷史時間,確立了對產業資本主義的監管體制。現在需要多少年來確立對全球化背景下的金融資本主義和製造業資本主義的監管體制呢?建立政府對企業的規制,首先需要強大的政府,但是在大眾民主下,又如何建立這樣一個強大的政府呢?如果沒有強大的政府,由誰來監管強大的資本力量呢?又有誰來制約民粹主義式的民主政治呢?也就是說,西方經濟體要達到內部各自經濟體的平衡很不容易,更何況說是國際經濟的平衡了。
西方沒有能力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非西方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是否能夠實現這個目標呢?對西方的失望,使得很多人把目光轉向發展中國家,包括金磚國家(巴西、俄國、印度、南非和中國)。但是,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能力,需要有客觀、冷靜和理性的認識。
拯救世界經濟 仍欠有效工具
以金磚國家為主體的非西方國家的崛起,的確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新一波全球化過程中,最顯著的國際經濟現象。在過去的20多年時間裏,這些國家的經濟取得了高速的發展,在世界經濟的版圖裏佔據愈來愈重要的位置。自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些國家也成為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不難理解,人們開始把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希望放到了這些國家。
不過,這些國家還遠遠沒有能力來平衡世界經濟。這裏有很多原因。和西方相比,包括金磚國家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規模和總量還是比較小。儘管在快速增長,但要平衡世界經濟的實際能力,必然受到其客觀經濟規模的制約。除了中國,其他國家的經濟規模遠遠小於西方主要國家。金磚國家中,其他四國經濟的總量相加還沒有中國一國大。金磚國家的總體經濟規模在擴大,也在產生一些外部影響力,但這並不自然轉化成為平衡世界經濟的能力。要平衡世界經濟,必須回到用什麼方式來平衡這個主要問題上來。在這方面,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問題都一樣:即使有實際能力,也缺失有效的工具來拯救世界經濟。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