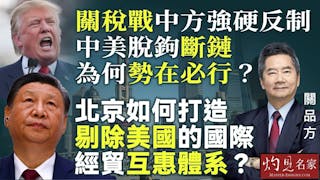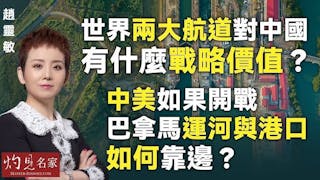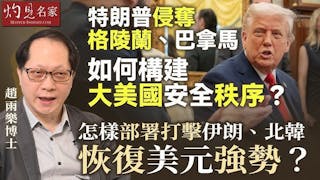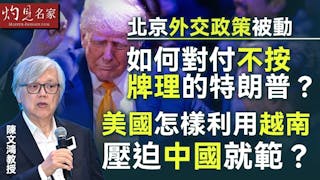世界在變,人們的思想也在變化。思想的變化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現實的變化,另一方面,變化了的思想,又會對現實產生巨大的影響。一旦人們接受了新的思想,就會影響到個人行為,無論是把思想作為目標來追求,還是作為行為方式來跟隨。在這個意義上說,通過觀察近年來亞洲的思潮變化,人們可以預知今後一段時間的發展新動向。
近年來,亞洲地區出現的最重要的思潮變化,概括地說,表現為三大方面,包括政治化和政治激進化、宗教思潮極端化和對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反思。
首先是政治化和政治激進化思潮。這裏其實包括兩個過程。第一個過程是政治化的過程,而第二個過程則是激進化的過程。就政治化來說,儘管很多問題實質反映的是宗教、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問題,例如收入分配差異、社會分化、經濟發展困境、就業不足、環境惡化等,但很多人希望通過政治化的途徑來解決。一旦遇到這些問題,社會的壓力一般上都是導向政府的。
再者,一旦政治化,則往往導致激進化。泰國、柬埔寨、緬甸、香港、台灣等國家和地區接連出現的政治激進化問題,都有此類情況。但實際上,這類問題用政治化的方式是解決不了的。通過激進政治來求得問題的解決,在很多情況下只是一種幻想。例如,在全球化時代,問題的實質更多的是資本而非政府。經濟發展需要資本,而資本需要好的生存環境。如果一個社會單純強調分配,資本就很容易跑掉;但如果只強調資本的利益,百姓就會很不滿意,政府因此必須在親商和親民之間達成平衡。很可惜的是,本區域所有的社會運動,無一不是以民主化為目標的、無一不是針對政府的,希望通過政治的民主化來實現社會所希望的公正和正義。但針對政府的社會運動無一不是在弱化政府。一旦政府被弱化,就愈沒有能力來達到資本和社會之間的平衡。
更為嚴重的是,本區域的政治激進化的表現形式與西方也很不一樣。近年來,西方國家尤其是西歐,也出現了政治激進化運動,有些運動甚至也很暴力,但是大多社會運動的表現是有限度、有妥協的。而亞洲沒有妥協傳統,社會運動一般都堅持不懈,會持續很長時間。泰國很典型。並且,一旦發生社會運動,法治就失去了蹤影,因為社會運動往往以道德自居,任意破壞法律。一些地方以民主名義推展政治激進化,實際上是反民主的。在亞洲,社會運動非要自己贏了才算數、才算民主。把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與最近香港的佔中運動作一個對比,就會很清楚。政府和社會運動之間的這種惡性互動,最終導致政治的不進步,甚至倒退。例如,泰國的政治民主運動最後以軍人政變收場;走了一個輪迴,毫無進步。今天香港的情況也是這樣。

其次是宗教激進化思潮的繼續崛起。亞洲很多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新疆,都出現了持續多年的宗教思想激進化。今天,宗教思想的激進化已經變成非常具挑戰性的全球問題。在中東,激進宗教思潮已導致無窮的政治衝突。失敗國家的形成或者政府愈來愈沒有治理能力,為極端宗教的崛起提供了機會。沒有人會相信中東的情況會很快好轉。隨着中東宗教激進思潮的崛起,這種局勢有可能延伸到本區域,尤其是那些治理能力不高的國家和地區。較之於其他地區,本區域的宗教本來具有溫和性質,但因為各種內外部因素,例如全球化、社交媒體、社會分化和收入差異巨大,很多年來宗教呈現出激進化的傾向。內部因素和外部影響的結合,有可能使得激進宗教運動變得難以控制。
反思新自由主義的弊端
其三是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傳播和對這一思潮的反思。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過去一直深受西方主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影響。日本過去被認為是亞洲模式的領導者,四小龍隨後。1980年代之後,日本按西方經濟模式來改革,但很不成功。今天,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安倍經濟學也已快走到盡頭了。其他一些經濟體,如香港和台灣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新自由主義導致和惡化了馬太效應,即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個經濟體的政府就面臨無窮的壓力。在全球化時代,資本可以流動,但政府不可流動,社會運動的壓力自然指向政府,而非資本。
幸運的是,亞洲很多經濟體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對社會所造成的衝擊。例如,中國在追求了數十年的 GDP 主義之後,已經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GDP 的增長對經濟和社會都很重要,但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實現經濟和社會之間的相互平衡。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曾經是最公平的經濟體,政府的合法性不僅來自於其推動經濟的能力,也來自於其實現基本社會公平的能力。現在,這些經濟體的收入差異愈來愈巨大,社會分化嚴重。如果這些經濟體不能改變這個情況,其統治合法性必然會受到挑戰。
當然,貧富懸殊並非僅僅是亞洲現象,而是一個全球性問題。目前的貧富懸殊問題是由資本啟動的,始於上世紀80年代由資本推動的經濟全球化。資本創造了巨大財富,但財富主要流向把握資本的少數人,大多數人沒有從財富的創造中獲益,有些甚至成了全球化的犧牲品。正如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其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所論證的,在全球化進程中勞動者只得到小頭,資本得到大頭,勞動者所得與資本所得完全不成比例。這是一個很危險的大趨勢。
從現在的情況看來,沒有任何有效的機制來阻止這種趨勢的繼續;並且現在世界各地都出現了政治的激進化運動。正如前面所說的,這些社會運動主要是反政府,而不是資本。其結果是,政府愈弱,資本的權力就愈大。資本、政府、社會三個權力之間需要達到均衡。但如何達到均衡呢?皮凱蒂認為,全世界政府要聯合起來。不過,如同馬克思當年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一樣,這個方法看似過於簡單和理想化。儘管經濟全球化了,但這個世界仍然處於主權國家的時代。如果人們不想放棄主權國家,每個國家都必須探討如何實現社會公平的問題;否則,各種激進化不可避免,社會變得更難以治理。
經濟治理制度的反思,也已成為西方和本區域的一大思潮。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後,西方出現了對自身制度、模式或治理能力的反思,其中對經濟制度和模式的反思比較多,人們試圖找到新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在經濟思想層面,人們提出很多有效的建議,主要是要提升政府在全球化時代管制經濟活動,尤其是金融資本活動的能力。西方現在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如何產生一個有效的強政府,來把這些思想轉化成政策和制度實踐。
在現實政治生活中,西方的大眾民主往往產生不了有效的政府。西方因此也開始從經濟的反思,轉向對政治的反思。這一點尤其表現在日裔美國學者福山的著述中。福山過去一直認為,西方民主是歷史的終結,會取代和終結所有其他的專制政體,成為統治世界的唯一政體。不過,近年來福山深入反思西方民主,分析西方民主為什麼會導向無效政府。當然,這種反思是一個大趨勢,並不僅僅表現在福山的著述中。西方世界反思本身民主的文獻在迅速增加。
實際上,把世界分成民主和專制本來就過於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任何社會如果要實現社會經濟的發展,都必須具備基本的政治秩序,而這樣一個秩序並非實現了西方式的民主就能保證的。在很多新興民主國家和地區,西方式民主很難提供一種穩定的政治秩序,來保證社會經濟生活的正常運營。不過,儘管亞洲一些民主政治已出現了很多問題,但總體上說亞洲的民主化仍然方興未艾。在對亞洲應當實行什麼形式的民主政治,缺少理論上的思考和實踐上的探索的情況下,亞洲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會繼續在民主化的道路上付出很高的代價。
不能盲目照抄西方
當然,亞洲也有成功的非西方發展經驗。包括亞洲國家在內的新興國家,應該怎樣得到發展和治理呢?福山強調的是三個要素,即國家能力、法治和民主責任制度。福山的觀點現已在亞洲流傳開來。然而,福山所強調的仍然是西方的經驗。從理論上看,這些要素並沒有錯,具有普世性;但如果要這些要素發揮實際的作用,就必須照顧到每一個國家和地區本身的文化條件。例如,在講政治責任制度時,西方民主國家強調的往往是政治人物對其選民負責,因為他們是選民選舉出來的,選票就是他們的政治合法性來源。但亞洲一些國家,包括一黨獨大的新加坡和一黨領導的中國,政治責任更多的是政府對民眾的自上而下的責任。從經驗上看,即使在西方,基於選票之上的合法性也已經遠遠不夠。一旦經濟形勢轉壞,政治人物很難作為。每個國家都必須根據自己的國情,選擇自己的發展和治理道路。
實踐上,照抄照搬西方模式,亞洲已經有很多的失敗例子,反而那些有意識抵制和避免西方模式的國家,更有可能取得繼續的成功。早先的日本是一個例子,今天的新加坡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儘管近年來新加坡也面臨和其他經濟體類似的挑戰,但新加坡選擇的是自己的模式,在不斷尋找平衡資本和社會利益的手段,例如新加坡的政聯企業和政府投資企業,在保障基本社會公正和公平方面,扮演了有效的作用。

另一個例子是中國和混合型企業制度。儘管經歷了大規模的市場化和民營化,中國仍然保留了龐大的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已經成為社會和經濟治理模式的重要一環。西方國家沒有類似中國那樣的國有企業,在調節經濟過程中,只有金融、財政兩個槓桿,不足以平衡市場的負面衝擊。中國和新加坡除了金融、財政槓桿之外,還有國企更為強有力的經濟槓桿。現在愈來愈多人看到西方的發展模式並不完善,任何模式都要隨着社會的改變不斷發展。中國的發展模式有其潛在的優勢。不過,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經濟制度,仍然具有巨大的改革空間。在目前的情況下,其社會功能沒有很好發揮出來。
亞洲社會有自己的發展邏輯。亞洲國家和地區過去成功的經驗,就是通過借鑒西方的經驗來塑造自己的模式。今天,如果要繼續取得成功,仍然需要在繼續學習西方的基礎上,繼續放棄盲目照抄照搬西方模式,尋求自己的發展模式。
原文刊於《聯合早報》,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