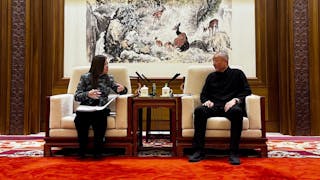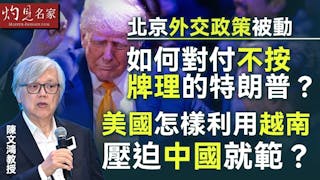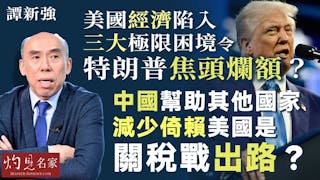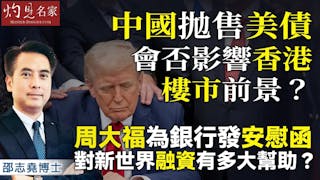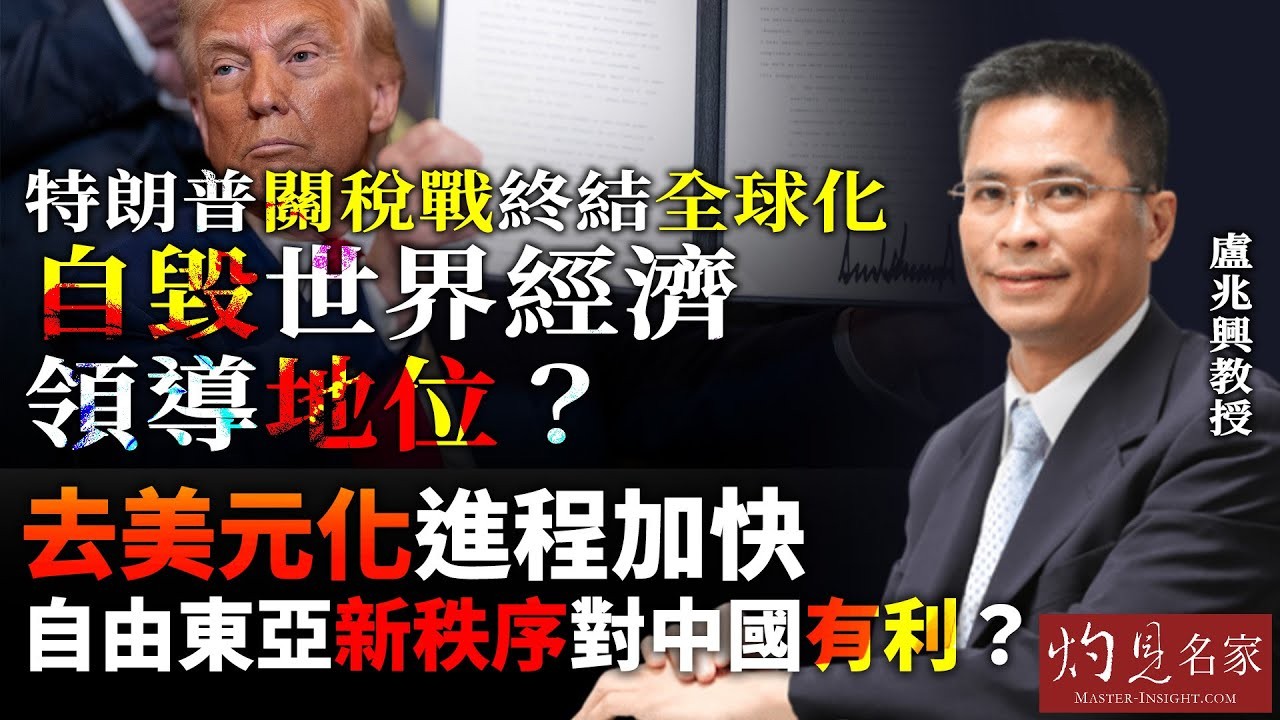自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特區政府成立至今快滿28年,自2002年實行的主要官員問責制(俗稱高官問責制)也將近23年了。然而,這個制度實行以後對特區管治、施政效率帶來什麼重要影響,其構想與現實、其推展的進度與廣度和深度,得失長短何在?是不是應該深刻以至全方位的檢視以至討論?
嚴重短板暴露
有人說存在就是合理的,但合理是相對的,並不等於必然,也不等於可以長久以至永遠持續下去。縱然香港公務員隊伍曾獲譽為世界第一流,人們特別欣賞其廉潔、高效,但別忘記這個基本是建立在高薪的基礎上,先不說位處最高層的行政長官,其薪酬遠高於美國總統以至中外幾乎所有政府首腦。就說公務員最高層級的D8,薪酬同樣是遠遠高於中外幾乎全部(略低於新加坡等少數國家)頂層公務員,其餘中上層公務員情況相近。然而,世界一等一的薪酬,不等於必定有一等一的表現和效率。這在應付社會重大問題以至突發危機方面,不時呈現以至暴露嚴重的短板。
當然,高官問責制的推行,在於回歸後首屆特區政府運作不暢,孤身一人出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未能得到以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這位原港英政府華人最高級公務員帶領的公務員班子配合,將相不同心,滿懷雄心壯心的董特首,競選特首期間廣泛接觸社會各界,集思廣益後提出連串新藍圖,包括希望香港長遠每年有85000個房屋單位建成,以達至七成港人能夠有其屋做業主,又針對香港長期存在的人才教育短板「高分低能」提出教育改革大計,亦就社會醫療福利等提出新猷,另提出發展創新科技、設立中藥港等鴻圖大計。

首屆行政長官孤掌難鳴
非常遺憾,董特首的改革熱情和構思,受到陳方安生為首的公務員團隊一面倒抗拒、抵制,甚至出現軟對抗以至冷嘲熱諷等傳聞。董特首陷於孤掌難鳴的境地。最明顯例子是1998年機場搬遷,一夜之間由啟德遷往大嶼山赤鱲角新機場,接力和配合欠周,出現倒瀉籮蟹的局面,事件引起一陣社會風波。各方原本以為,公務員團隊原班過渡,董建華與陳方安生組成的「董陳配」,應該可以合作愉快,帶領香港繼往開來,有效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
另一方面,政府日常運作和管理下出現的缺失迭現,政府對外界的政策解說一直被批評為表面和僵化,上情下達以至下情上達都不盡人意,不時令訊息被誤解,甚至被居心不良的人士刻意曲解。政府回應社會訴求時,往往出現後知後覺的情況,無形間令說服力打折扣,給市民造成負面甚至惡劣觀感。而2000年後,社會發展變化急劇,帶來的新要求和新挑戰,政府繼續以既有管治思維和應對慣性顯然難以招架,稱得上是「急驚風遇着慢郎中」。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更是普遍觀感。
為改進管治,特別是有效落實行政長官施政宏圖,包括對有關部門的了解和主要政策的的掌握,因而有問責制的醞釀與籌劃,並由2002年第二屆特區政府開始推出,與每屆特區政府任期一樣是五年。由是,按範疇而設決策局,對應或對應公務員有關部門,例如佔政府開支佔前三的房屋、教育和衛生福利,各決策局局長與政務司司長、公務員事務局局長等組成問責班子,其下有副局長、政務助理等。問責官員包括特首委任社會精英以至公務員隊伍有興趣者轉任,應該說都是希望有一番作為的。

問責制成效迄今不彰
轉眼間,問責制也推行了23年,問責班子換了一個又一個,只可惜問責成效迄今不彰,而特區納稅人支付的問責班子的款項,23年,少說也有20多億吧,也該到了衡工量值的時候吧。
先說改進管治,提高績效,恐怕遠遠達不到。近期政府為減少赤字而決定提高違例泊車罸款,竟然才發現原來這些「牛肉乾」竟然超過30年分毫未加。那麼,過去幾屆的運輸及房屋局以至發展局等部門,對這問題有討論和研究嗎?曾經討論的電子道路收費為什麼總是不了了之?再如資助大學本科生學費,自1998年起,竟然都維持在每年42100港元的水平,從教育統籌局到教育局,20年間換了四個局長,都沒有注意到要適當提高學費。至於衛生福利局,第一屆下半期和第二屆全期合計八年間,竟然完全沒有規劃要增建一間公立醫院,而香港人口和醫療需求卻持續上升。
如果說問責官員多是五年一屆,頭一、兩年熟悉工作環境、與團隊以至公務員運作要磨合,之後兩、三年也該有所作為吧,只是不少決策局和相應的公務員隊伍仍是原地踏步。最明顯的例子,是食肆和屋苑廚餘回收試行了一次又一次,計劃反而縮小了規模;垃圾徵費討論又試行,結果2024年宣布擱置。再者,不少問責官員是蟬聯的,一些副局長做足五年後升任局長,同一個部門高升了,薪酬當然水漲船高,可惜其政績不見得亮眼,甚至是碌碌無為。再者,近三屆問責高官是離開公務員隊伍而轉任,照道理和事實上他們熟悉公務員運作,對政策推行的長短機危以至難點痛點,不可能說不清楚或者不知道,但就是有幾位公務員轉職的表現不稱職,令人搖頭嘆息。
識變、求變、應變,是中央對香港的期許,也是本屆特區政府的自我鞭策,那麼推行了23年的問責制,是不是也應該作出深入、徹底的檢視和衡量呢?既然從社會以至公務員隊伍網羅了那麼一大批問責官員(以及配套的政務助理和文書),政策初衷與現實、問責成效與期望,有沒有出入或落差,是不是也要識變、求變以及應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