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中國作為大國 需要怎樣的現代產業體系?〉(二之一)
就經濟發展要素而言,從低度到中等發展水平的過程相對比較簡單。在發展早期,經濟要素成本低廉,包括工作力和土地,人們對環保的要求也不那麼高;更存在着大量的經濟增長空間,包括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房地產、通過現有技術的應用而來的製造業等等。只要找到啟動發展的資本,配置於有效的政策,就可以實現增長。在這個階段,對企業來說,做什麼都可以賺錢。
中等收入陷阱難避免?
這個階段發展,推動一個經濟體從低度到中等收入水準。但是,從中等到高等收入水平的過程,則比第一個階段要困難得多。一是生產要素成本提高,二是新經濟增長空間匱乏。學術界和政策研究界因此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世界銀行《2024年世界發展報告》再次更新了其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研究,發現各國隨着財富增長,通常會在人均GDP達到美國年度水準10%左右時──相當於今天的8000美元──掉入世行所定義的中等收入陷阱。自1990年以來,僅有34個中等收入經濟體成功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其中超過三分之一,要麼得益於加入歐盟,要麼得益於新發現的石油資源。
今天,中國的人均GDP在13000美元左右,離跨越中等收入水平和進入高收入經濟體已經是一步之遙。在東亞,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包括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台灣和香港)。這五個經濟體的成功主要是實現了可持續、基於技術進步之上的產業升級。這些經濟體在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後,大量投入科創,幾乎每十年實現一次重大的產業升級。如果沒有產業升級,那麼很難想像他們是如何成功的。如果說他們的政策是成功的,那麼成功的核心就在於促成了技術進步,不僅促成了傳統產業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增加新的經濟活動。對社會來說,新增經濟活動擴大了就業,勞動者增加收入,中產規模持續擴大;對政府來說,增加稅收,有能力擴大對科研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

科技創新的三架馬車
我們的研究團隊經過多年的研究,提出了科技創新的三架馬車,即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和金融服務。我們總結了自近代工業化以來不到300多年的經濟發展史的經驗,發現這三者缺一不可。當然,各國情況不同,尤其在早期,三架馬車不見得能夠均衡發展,因為很多國家根本不具備客觀條件。三架馬車有機配合和均衡發展的典型,是二戰之後的美國,因此,直到今天美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也是最強大的。其實,那些長期陷入低度發展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大都可以通過這三架馬車的框架得到解釋。
一、基礎科研:一般來說,基礎科研的主體是大學和研究機構。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研究活動一般都是基礎科研。基礎科研不是資本密集型的,而是興趣和自由密集型的。國家需要為其科研群體(或者科學人口)提供一個體面的中產生活,給他們足夠的自由去追求科研興趣。在當代,政府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不僅需要資助大學和科研機構,更需要創建基礎科研所需要的實驗室等。
二、應用技術轉化: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是企業。在西方,應用技術的轉化主體是私營企業,即使政府想要搞轉化,也是通過競爭方式委託給私營企業;美國的軍工複合體便是典型;日本和韓國等經濟體也是這樣的,只不過政府發揮了更大的作用。在蘇聯,國有企業承擔了這一角色,但因為缺乏競爭機制,沒有實現可持續性。
三、金融服務:金融服務的主體一般是金融機構。政府通過財政系統支持基礎科研沒有問題,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是這樣做的。當然,在發達國家,很多私營企業也以不同方式自己搞基礎科研,或者大力支持大學和研究機構。但政府很難支援應用技術轉化,因為風險極高,政府很難用納稅人的錢去做那麼高風險的事情。同理,傳統銀行也很難用存款人的錢去進行。因此,二戰以來,美國發明和創造了風投體系,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二戰以來最偉大的金融發明。
因此,三架馬車把教育(科研和人才培養的主體)、應用技術轉化、企業和產業化一體化了,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產、學、研、政一體化,理順了科創的整體邏輯,可以稱之為「大科研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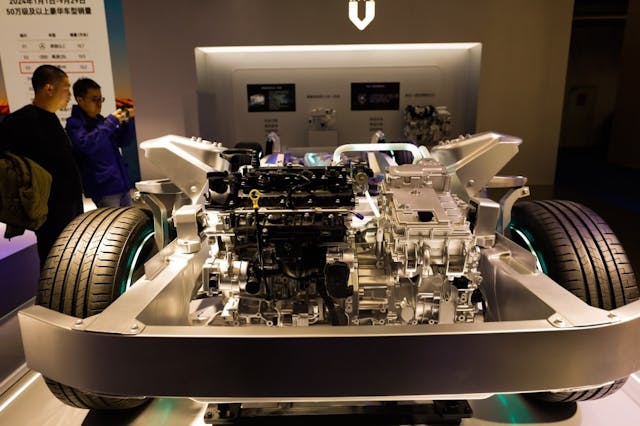
下一步 怎麼做?
因為制度背景不同,各國都需要根據實際情況來設置科研體系,但不管什麼樣的制度背景,都必須符合科創的基本邏輯。我們這裏所說的制度背景主要是指三架馬車在不同國家體現為不同的主體的問題。
正是因為意識到「大科創」的重要,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礎和戰略支撐,並把這三者放在一起加以論述,因為在中國的管理體系中,這三板塊一直是分割的,教育屬於教育部,人才屬於人社部;而科技更加分散,散布於科技部、工信部和發改委等部委。
憑經驗看,儘管正確的論述和管理構架有了,但這三塊要有機整合成一個大科創體系,依然需要很多的努力。這要求我們首先必須從大科研體系的要求出發來看,現在制度要素哪些方面還存在短板,或者還沒有理順。我們可以列出一個很長的清單,必須強調的是,這些現象是普遍存在於各地。
教育、人才、科研這三者還是由不同的政府部門負責。儘管有協調機構的存在,但力量非常單薄,行動主體依然是各個部門,並且彼此各自為政的情況還是非常嚴重。
科研管理的問題更大更多,首先是人才的定義。人才基本上還是以人們所說的「帽子」來定義的,而那充其量是以研究成果來定義,過分強調學術人才,大大忽視了應用性,尤其是工業人才。在基礎科研領域,這種定義並無大礙,但一旦到了工業領域,這種人才定義顯然是不科學的。只有在基礎科研轉化成應用技術之後,才會成為具體的經濟活動。換句話說,我們只看到了那些獲得諾貝爾獎的人才,而忽視了類似馬斯克、比爾蓋茨、奧特曼、黃仁勳那樣的人才。實際上,這次杭州六小龍企業中的這些人才,並不在我們的人才名單上。
現行人才定義也影響了科研經費的分配取向。大量經費投在那些已經有了帽子的人才身上,往往是比較年長甚至老齡人才,而年輕群體則得不到足夠的科研資助。儘管國家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也為年輕群體設立了一些專案,但因為分配者依然是具有帽子的群體,因此年輕群體缺乏資助的情況依然嚴峻。比較而言,美國大量資助流向年輕而非年長群體。考慮到人類自進入互聯網時代以來,年輕群體已經佔據基礎科研和應用技術轉化的主體,如果這種情況不改變,很難實現具有突破性的科創。

人才定義也影響到科研的定義。在學界和業界,很多人對科研和發表論文之間的關係有錯誤的認知,把發表論文和科研等同起來。為了追求學術,大多研究者都在發表論文,而非科研。因此,儘管我們發表的論文數量大增,但轉化率非常低。原因很簡單,研究者的目標是發表論文,而非真正的科研。這種情況又涉及到教育和科研部門的評估體系。這個體系依然存在太多的問題,更多的是體現官僚精神,而專業精神依然很低,甚至缺失。
就科研的工具來看,我們眾多的科技實驗室都呈現為一個個土豆,互不關聯,互不開放。儘管理論上產權都屬於政府,但實際上的使用權呈現出過度的私有化,甚至是個人化性質。儘管國家實驗室愈來愈多,但大部分實驗室使用不足,造成過度浪費。如何把實驗室的多而不強轉型成為又多又強呢?這需要系統性的體制改革。
在技術轉化端也存在諸多問題。沒有對產學研過程有科學的理解,現在一些部門鼓勵甚至要求做基礎科研的人也要去做技術轉化。這相當於要求一個科研人員既要做基礎科研,又要做技術轉化,同時還要去籌錢。儘管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但從經驗來看,這樣做成功的案例少而又少,在任何國家都是如此。更為嚴重的是,這樣導致了基礎研究應用化,不利於基礎科研本身的發展。
應用技術的人才也是一個問題。理論上說,專業技能人才的培養和培訓已經得到足夠重視,但這種重視並沒有轉化機制。職業學校沒有納入人才培養系統,它們缺乏好的要素,包括政策、人才、資源等等。因為得不到實際上的重視,很難產生工匠,更難有工匠精神。儘管從產業升級和科創而言,這個領域的人才愈來愈重要,但國家最大量的資源依然在高等教育。這次很多人把杭州的成功歸功於浙江大學,浙大當然很重要,但絕對不要忘記浙江理工等大學在這個過程中的關鍵作用。浙江高科技企業,包括阿里巴巴,很多人才並非來自浙大。
在創新領域,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還沒有理順,沒有確立在分工的基礎上推行的合作制度,這裏既包括國有和民營企業之間的關係,也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尤其在金融支援方面。嚴格說來,我們還沒有形成一個能夠支撐科創的金融系統。國家並不缺錢,缺少的是一個有效的金融系統。儘管已經確立了「金融強國」的命題和目標,但還沒有體現在金融體系的設計上。無論在企業還是城市層面,凡是搞投機性金融的不僅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更會出現大問題,但凡是投資技術創新的,最終都會孵化出新技術,以及基於新技術之上的新經濟活動。
連接產學研的是一整套體制機制,這方面的改革亟待加快。中國的技術發展路徑和東亞其他經濟體,尤其是日本和韓國的,並沒有多大的區別,早期是應用技術,隨着技術的積累,逐漸轉向原創。今天的中國在諸多領域,尤其是生物醫藥、互聯網和人工智慧領域,正在出現大量的原創性技術,但因為監管過度或者不科學,使得這些技術不能落地,很多流落到海外。換句話說,我們自己產生的很多新質生產力正在流向可以落地的經濟體。
必須意識到,美國矽谷三分之二以上的獨角獸企業領袖來自一、二代移民,其中也有不少來自中國。考慮到新的經濟活動需要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來獲得,這些技術的流失就導致了新的經濟活動不足。這也是前面所討論的內卷成原,因為所謂的內卷,就是對存量經濟活動的競爭。即使偶爾產生新經濟活動,但因為種類過少,導致各地一哄而上的局面,目前低空經濟的競爭就是這種局面。 這種情況只有透過增量經濟才能解決。

兩個關鍵問題
當然,類似這樣那樣的問題可以有一個無窮盡的清單。 問題是怎麼辦?有兩個關鍵問題需要考量。
第一,需要盡快確立一個大科研體系。如前所述,國家層面理念已經有了,但落地依然需要自上而下的體制機制改革。這是政府的責任,大部分國家都是如此,包括二戰之後的美國。儘管自下而上也可以形成這樣的體系,但這需要漫長的時間。在國家間競爭愈來愈激烈的今天,是很難想像一個完全自我生成的大科研體系的。
第二,需要進行試驗區式的改革,即需要設立科研科創特區。在我們條塊管理的體制內,很難通過「條條」(按:中央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垂直權威線)發生有效的改革,因為條條的改革牽一髮動全身,很難掌控局面。這些年各地都有一些改革,但很快就會發現改革不下去了。在「上下一般粗」的體制內,改革涉及到太多的部門和政府,任何改革都會最終導向碎片化和分割化。
因此,有效的改革要從「塊塊」(按:省級或地方一級政府的橫向權限)推行,此中以新加坡、沙特等經濟體的改革特別值得參照。儘管這些都是很小的經濟體,但也是通過「塊塊」方式推進改革的。 中央政府給予「塊塊」充分和完全的授權。因為這種授權往往是一籃子的,而非通過中央各個部門,「塊塊」改革和所產生的科創系統體現為系統有效性。再在此基礎上,向國家其他地方擴散和推廣。中國早期的特區就是以這種方式進行的,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應當指出的是,「塊塊」既可以體現為一個特定的地理區域,也可以體現為一個功能領域。
杭州的成功也可以視為是「塊塊」改革的成功。杭州的高科技集中在餘杭和濱江兩個區域。下一步,我們可以圍繞第四次工業革命所需的要素,在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和成渝等具有良好創新生態的地區設置多個表現為「塊塊」科創特區,根據不同技術領域的需要,設立各類科創特區,真正實現產學研一體化,再向周邊地區輻射和擴散,成為區域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主動力。
例如,深圳的互聯網和人工智慧高度集中在南山區,南山可以設立地理區域意義上的、以互聯網和人工智慧領域為核心的科創特區;再如廣州集中了大量的醫院並且生物醫藥比較發達,廣州可以設立醫藥功能領域意義上的科創特區。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杭州、南京、蘇州、成都、重慶、西安、蘭州等很多城市,都可以找到類似可以設立科創特區的「塊塊」。在這些「塊塊」,國家賦予真正實現基於三架馬車之上的產學研一體化的各項政策,以期取得突破性的科創,在引領未來產業的同時賦能現存產業。
今天,我們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美國正在籌劃「馬斯克式」的體制機制改革,一旦成功,就會對科技界帶來巨變。我們也會在各個層面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壓力。唯有改革,才能進步,這是一個普遍的真理。
現代產業體系 2-2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