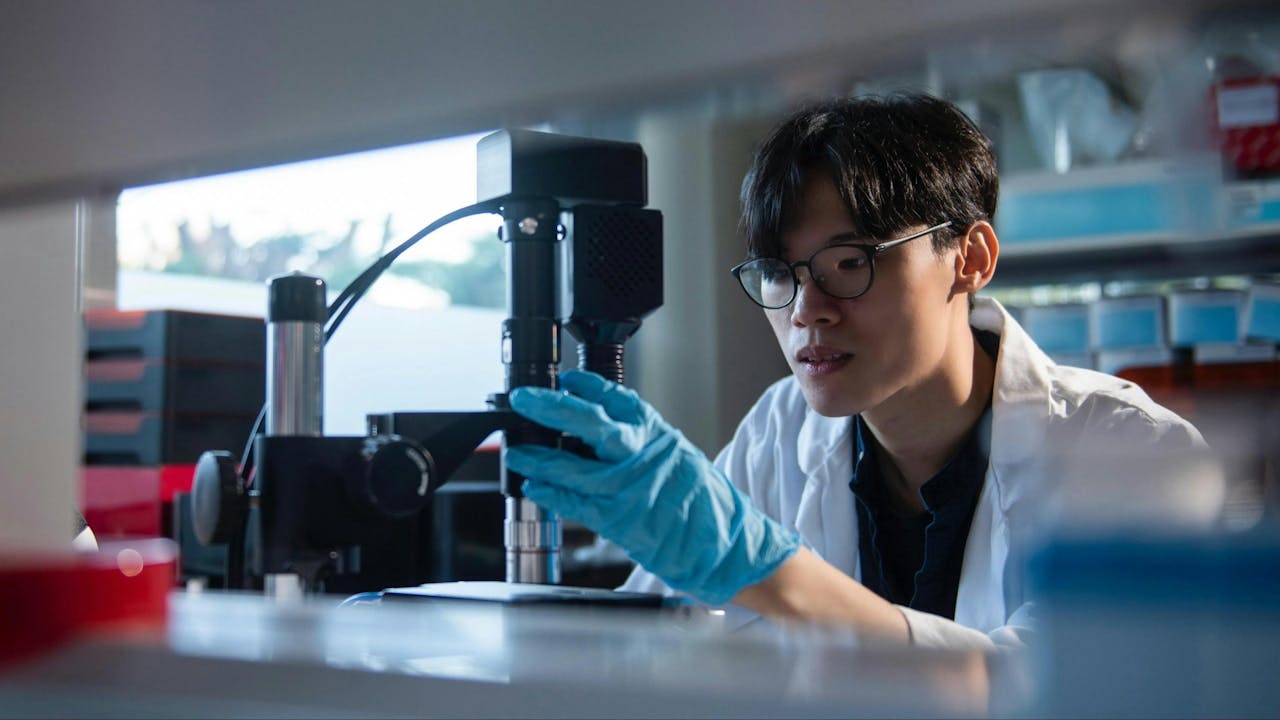「科研從來不只是一條學術的獨木橋,而是探索知識、創造影響的多重旅程」,這是呂錫進(Danson)的信念。作為裘槎基金博士獎學金及香港賽馬會獎學金的得主,他從香港科技大學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學士、分子生命科學碩士,到在牛津大學攻讀癌症基因組學博士,就學足跡橫跨亞歐的頂尖學府。然而,對於科研與未來發展,他更關注如何將知識轉化為真正造福社會的力量。
參賽確立科研應用志向
呂錫進的目標並非一開始便清晰明確,而是經多次選擇與調整逐步成形。他最初在中學階段選修商科,認為這是一條穩妥的道路,且能避開自己較為抗拒的數學。然而在學習過程中,他發現商業理論缺乏能夠真正引起他共鳴的內容,相比之下,生命科學所帶來的探索感與實際應用價值更吸引。由於學校制度所限,他未能在高中階段轉科,直至入大學後,才正式踏足生命科學的領域。
他回憶道,對生物學的興趣,來自於對生命本質的好奇,相較於商業理論,他更能在生命科學中看到知識與現實世界的緊密聯繫。這種轉變並非一蹴即就。就讀科大期間,他參與了國際基因工程機器設計比賽(iGEM),首次接觸到合成生物學,並體會到跨學科研究的魅力。在這場競賽中,他學習如何將生物學、數學建模與程式設計結合,理解科研不只是紙上談兵,而是實踐綜合能力,由此確立了自己的方向,決心投身更具應用價值的科學研究。
「有時候選擇不是由我們主導,而是環境為我們開啟了新的可能。」呂錫進形容自己確立方向的歷程。這啟示大家的是,學習與職業選擇並非僅限於最開初的決定,而是在探索與實踐中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道路。


從高壓驅動到自律探索
呂錫進先後在香港與英國接受高等教育,讓他對兩地的學術文化有深刻體會。他指香港的學術環境特色為高強度管理,導師會頻繁設定目標與死線,確保研究進度,學生則習慣在外部壓力下推動自己前進。這種模式確保了學術成果的產出,但也可能削弱學生的自主探索動力。
當他來到牛津大學後,發現這裏的學術文化截然不同:「導師不會催促進度,一切全憑學生的主動性,沒有人會推動你,你必須學會推動自己。」在這樣的環境下,他開始思考:「如果沒有人監督,我還會繼續這條路嗎?」
這一轉變讓他意識到,真正的學者,並非為了交功課而學習,而是為了探索未知而前進,研究的本質對知識的持續追求。
博士生涯的挑戰
「學術界的晉升從來不是單靠學術能力,還需要策略、資源、關係和時機,你便會開始思考,這是否唯一的出路。」呂錫進坦言博士生涯讓他深刻理解科研的現實。他表示博士畢業後,許多人需經歷長達六至八年的博士後研究(Postdoctoral Research),才能競逐有限的教職,而這些機會的供應遠少於博士畢業生的數量。
學術界的競爭不僅來自知識的突破,還來自資源的爭奪。研究經費有限,許多科研人員需投入大量時間撰寫研究計劃書,競逐資助,甚至面對職位不穩定的困擾。
於是他開始探索其他可能,嘗試進入生物科技產業及創投領域,希望了解學術研究如何轉化為產業應用。他曾在生物科技風險投資機構實習,研究投資人如何評估科學技術。


頂尖獎學金的意義
獲得裘槎基金博士獎學金與賽馬會獎學金是榮譽與肯定外,也提供全額學費與生活資助,還包括額外的研究資金,甚至創業或學術發展基金,支援學者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
呂錫進認為,即使獲得最頂尖的獎學金,仍無法改變學術界的結構性挑戰,例如晉升困難、學術資源分配不均,以及科研成果如何進入市場等問題。
留英發展還是回流香港?
對於未來,呂錫進積極探索產業研發、創業,甚至回流香港的機會。他表示歐美的生物製藥產業發展成熟,提供大量高薪研發機會,而香港的生物科技產業雖然仍在發展初期,但具備政策支持與市場潛力。
然而他也深知回流發展的挑戰:「香港的科研產業仍在起步,資金、技術轉移、產業鏈等方面仍須完善。」這讓他對未來的抉擇更為慎重。
他認為真正的科研信念,不僅是發表論文:「學術研究的價值,不應只停留在實驗室,而是要進入產業,影響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