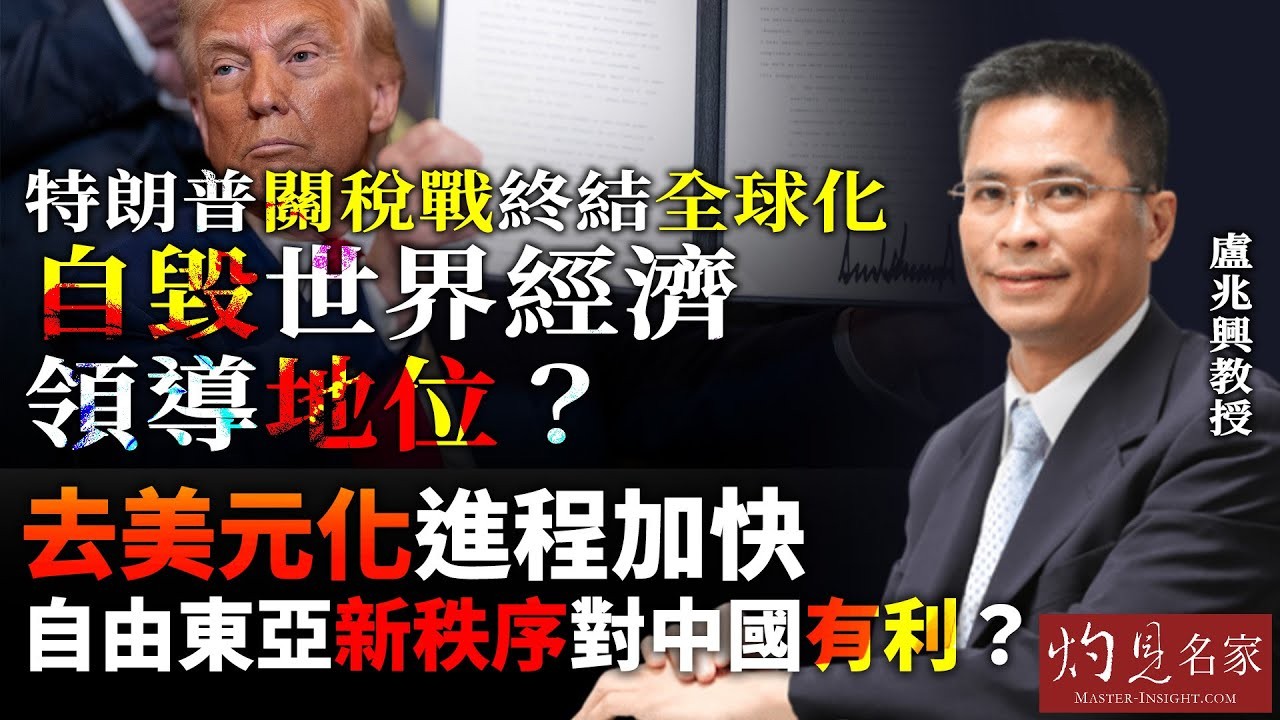寒流來時,我總想起芬蘭。
連續7年蟬聯聯合國研究「全世界最快樂的國家」,芬蘭冬天長達5個月,每天日照只有6小時,今天赫爾辛基零下5度。
這⋯⋯怎麼快樂得起來?
與其說芬蘭人最「快樂」,不如說芬蘭人最懂得面對「不快樂」。
總結芬蘭民族性的一個字,叫「sisu」,可翻譯成「面對逆境時的決心」。不管碰到什麼問題,不抱怨,用耐心、意志力,往前走。芬蘭人喜歡說:「堅持的決心強到,可以穿透花崗岩。」

Sisu,把寒流,變成暖流
Sisu的代表性人物,是Veikka Gustafsson。他不用氧氣桶,登上包括聖母峰的14座八千公尺以上的高峰。他對sisu的詮釋是:「習慣性地再推自己一把。只要水還沒結冰,就跳下去游。一開始很不舒服,當作是難得的體驗。一會後就會習慣。事後會覺得很美好。」
Sisu,把寒流,變成暖流。
很高的境界!但我不禁也想:
活着一定要登上聖母峰、穿越花崗岩嗎?在海平面上把一家子顧好,難度和意義,比不上一個人登上八千公尺的高峰?如果只靠「決心」,會不會辜負了心的其他層面?
Veikka Gustafsson自己也承認,sisu的風險是變得固執、愛面子,無法示弱或求助,嚴以律己也嚴以待人。
幸運或不幸的,大部分人都無法登上聖母峰。我們sisu的程度,頂多只到基地營。
而大部分人安身立命的原則,沒有像sisu這樣一個鮮明的字眼。那些求生法則,沒有名字,像一個沒有地圖的景點、鮮少被報道的小鎮。

如果硬要給它一個名字,可以說是 「掙扎」。往上到聖母峰的力道不足,往下回基地營的風勢強勁,但也不輕易放棄,每天該幹什麼還是幹什麼。
那是一種無重力的狀態。漂浮在成功與失敗的半路,不管往前或往後,都有點身不由己。但一公尺一公尺地,還是畢業了、就業了、成家了、把孩子養大了。
掙扎中,我們沒膽到冰水游泳,但努力讓自己柔軟如水。無法穿透花崗岩,但想辦法以柔克剛。不管對自己或別人,「嚴格」少一點,「風格」多一些。
很喜歡住在芬蘭的朋友翠珊拍的這張照片。雪地與太陽,看似矛盾,卻和諧共存。就像寒流與暖流、快樂與不快樂,總是共存在每一天,就看我們如何調配。
明早低溫,一定冷得不想起床。但賴個10分鐘,終究還是會刷牙洗臉。
寒流中做好保暖,就是暖流。不快樂時保重自己,就是快樂。新的一年,把一件有意義的事,無中生有做到好,就是聖母峰了。
原刊於作者Facebook專頁,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